核心摘要:2025年已近尾声。早起推窗时,薄薄的寒气漫了进来,贴着人的面颊,清冽而又温柔。天是那种腌过似的淡青色,云絮疏疏的,像谁用极淡的蓝色,在偌大的画纸上,不经意地扫了几笔。窗户外的银杏树,叶子大部分已落尽了,赭黄的枝桠伸向天空,瘦硬而遒劲,仿佛一阕戛然而止的旧词,韵脚都凝在空气里。远处传来一两声零落的鸟声,...
岁末书房记
周争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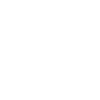
2025年已近尾声。早起推窗时,薄薄的寒气漫了进来,贴着人的面颊,清冽而又温柔。天是那种腌过似的淡青色,云絮疏疏的,像谁用极淡的蓝色,在偌大的画纸上,不经意地扫了几笔。窗户外的银杏树,叶子大部分已落尽了,赭黄的枝桠伸向天空,瘦硬而遒劲,仿佛一阕戛然而止的旧词,韵脚都凝在空气里。远处传来一两声零落的鸟声,暂短而沉闷,倒像是岁末带着倦意的叹息。哦,又一年了。这叹息落下,并不消散,只静静地沉积在心房的某个角落,与经年的尘埃同眠。
回到室内,地暖散着些微微的、烘烘的热。这儿是我冬日里盘桓最多的地方。吃过早餐后,我便开始在这斗室里,打发一天的时光。
不大的斗室里,日光被窗棂裁成斜斜的一方,恰好落在画架旁的地板上,像一块温润的旧玉。画架立在窗户下,画板上夹着洁白的水粉画纸,等待着第一笔色彩的降临。调色盘已斑驳陆离,前日未洗的湖蓝与熟褐结成丘陵地貌,新的颜料挤上去,鲜活得像是刚从大地深处采掘的矿石。画笔斜插在笔筒中,鬃毛微张,保持着最后一次与画纸对话的姿态。当我的手指握住笔杆时,时间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流淌——不再是钟表刻度,而是造型与色彩的律动。蘸取颜料时发出的轻微“噗”声,是这场仪式开始的序章。笔尖触及画纸,那沙沙的声响,如春蚕食叶,如细雨润土。有时我会停驻良久,看阳光如何缓慢移动,改变着静物上高光的位置,那分明是光阴在我眼前具象地行走。颜料层层叠叠,堆积出风景的肌理;排笔抹过,又掀起记忆深处的潮涌。在这过程中,我甚至能听见色彩在对话:默绿的低语,天蓝的宣言,土黄的沉吟,它们争执、和解,最终在画纸上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如同万物在宇宙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
而画架旁边的书桌,则是另一种气象。木质桌面上墨迹点点,像深夜的星空。稿纸铺开,素白如待耕的田野。钢笔卧在一旁,金属笔尖在光线下泛着幽蓝的光。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的写作往往不像作画那般仪式化——可能只是一个词的突然造访,像不知名的鸟雀撞进窗来。当笔尖开始在纸上行走,沙沙声便响起来了,那声音比画笔更轻,更密,如蚕食桑,如雪落湖。字句从意识的深处浮出,有的清晰如刻,有的朦胧如雾,需要捕捉、驯服、安放在合适的位置。有时我会停下,望向窗外那棵银杏树,看风如何把仅有的几片叶子从枝头慢慢松开——而就在这凝视的瞬间,某个恰当的比喻悄然降临。删除时,橡皮屑卷曲着落下,像极了旧时光的碎屑。重写时,新的字迹覆盖旧的,如同新的记忆覆盖着老的,却总还能隐约看见底层的纹路。写作是一场与无形之物的角力,词语是唯一的绳索,而意义的深渊,永远在下一页等待着。
有趣的是,这两种创作常在这斗室里相遇、交织。午后,当我从画架前转身,带着满手未干的颜料走向书桌,那鲜活的色彩气息便混入了文字的世界。有时画中无法言说的情绪,会在笔尖找到出口;有时文字里纠缠不清的意象,竟在调色盘上豁然明朗。它们互相注释,彼此成全——画是凝固的文章,文章是流动的画。阳光从东墙游走到西墙,见证着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创造如何在这方寸之间此消彼长,如同潮汐的涨落。
有时,我放下画笔或钢笔,静静坐在两者之间。画架上未完成的山川在月光下泛着幽微的光,稿纸上未结尾的句子如待续的乐章。水粉颜料的气味渐渐沉淀,稿纸的清香又浮上来,它们在空中交融成一种独特的气息——那是冬日斗室本身的味道,混合着困惑与顿悟,挣扎与释然。在这气息中,我仿佛听见色彩与文字在低语,它们讨论着光影的走向,斟酌着句读的节奏,共同编织着这斗室之外的、另一个更辽阔的世界。
小小的空间因此不再局促。当画笔挥洒,它延伸成无垠的原野;当文字流淌,它拓展成时间的河流。四壁悄然隐退,唯自娱自乐的光芒,在这斗室中央,安静而炽烈地燃烧。
(作者系湖北省省直机关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