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摘要:初冬的大洪山,重峦叠嶂。寒风漫过林梢,红橙叠翠,层林尽染。红的是枫,褪了盛夏那份灼人的烈性,成了陈年旧锦似的暗赭,里头又隐隐透着些不肯熄尽的火;橙的是槭,一簇一簇的,像薄暮时分最温柔的那抹云霞,不小心被山林挂住了;绿是经了霜的松与柏的苍黛,沉沉的。至于黄,那是主角了,是莽莽苍苍的背景里忽然跳出的一星...
大洪山的银杏
周争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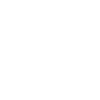
初冬的大洪山,重峦叠嶂。寒风漫过林梢,红橙叠翠,层林尽染。红的是枫,褪了盛夏那份灼人的烈性,成了陈年旧锦似的暗赭,里头又隐隐透着些不肯熄尽的火;橙的是槭,一簇一簇的,像薄暮时分最温柔的那抹云霞,不小心被山林挂住了;绿是经了霜的松与柏的苍黛,沉沉的。至于黄,那是主角了,是莽莽苍苍的背景里忽然跳出的一星亮,一片光,一坡的金箔,在铅灰色的天穹下,自顾自地辉煌着。我的脚步便不自主地朝那最亮的一处黄寻过去。
走近了观看,那黄才显出它的层次来。有些是初熟的枇杷那种嫩嫩的鹅黄,有些是阳光滤过蜜蜡那种半透的琥珀色,还有些已在边缘上蜷起焦黑或褐色的倦意,像一篇华美文章终结的句点。风不大,只是悄悄地贴着山脊掠过。一片片扇形叶子,便悠悠地告别枝梢。它不像别的树叶那般慌慌张张地扑跌下来,而是打着旋,左一下右一下地飘落,仿佛一位谢幕的舞者,用尽最后的气力,在虚空里画着依依不舍的弧线,落在先前已铺了厚厚一层的同伴身上。很快,它的身影便给吞没了,只剩一片软软的寂静。这寂静是蓬松的,踏上去,脚底传来一种极温柔的、簌簌的叹息,仿佛大地本身,正做着一个关于消逝的、金黄颜色的梦。
我便在这片杏黄的而又厚实的“地毯”上停下来,盯着眼前那棵被栏杆围起来古老的银杏。它的树干粗砺得惊人,厚厚的树皮像是凝固了的、深褐色的时间。那上面纵横的沟壑,是风雨用几千年的耐心,一刀一刀镌刻上去的年轮。仰起头,看那嶙峋的枝桠伸向天空,像无数只苍老而固执的手,向虚空里攫取着什么,又像是要将这满身的岁月,无言地摊开来,告诉过往的流云与飞鸟。它就是历史,饱经风霜。我猜想,秦汉的月色,曾冷冷地浸透过它的每一片叶子;唐宋的雨声,曾耐心地叩问过它的年轮;明清的风霜,曾无情地侵蚀它的身躯。至于那些千百年来来往往的人,筑室的,征战的,吟诗的,樵采的,都不过是它脚下匆匆的过客、模糊的影子。而它只是站着,春来便萌一树翡翠的梦想,秋尽便抖落一身灿烂的荣光。个体的生命,在它面前,短暂得如同这刚落下的一片叶子,方才还在枝头招摇着全部的世界,转瞬便委身于泥土。这是何等的令人沮丧,又是何等的令人肃然。
风又起了。这一次,掠过树梢时,带起一阵更繁密的沙沙声。无数的黄叶,像一群终于得到号令的金色鸟雀,挣脱了最后的牵系,纷纷扬扬地开始了它们一生中最后一次的飞翔。它们在空中交织、碰撞、分离,将一片死寂的、灰白的天空,搅动成一片活泼的、流光溢彩的生命的漩涡。这景象里没有悲戚,只有一种盛大而庄严的仪式。我忽然明白,那千年的老树,它并非漠然。它是以整棵树的存在,来参与这年复一年的挥霍与告别。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具体的、鲜活的瞬间;而它自己,则是那承载了所有瞬间的、沉默的永恒。
眼前的黃叶,还在簌簌地落着。它们盖住了来时的小径,也终将盖住我此刻停留的足迹。然而我并不觉得凄凉。这满地的灿黄,并非银杏叶的坟墓,而是一张辽阔无垠、温暖柔软的眠床,是生对死的一种最慷慨的铺垫,是时光为自己织就的一袭华美的袍。凋零与长存,须臾与千古,在这里并非对立,而是像这树的根与叶,互相寻找,互相成全。每一片黄叶的飘落,都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对过往的告别,对新生的期许。
下山的时候,我没有回头。但我知道,那一片浩浩荡荡的、寂静的金黄,会一直铺到我的梦里去。而梦外,那棵千年的老树,依旧站在初冬的寒风里,准备做下一个春天的梦。
(作者系湖北省省直机关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