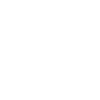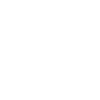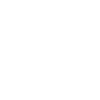游客在故宫太和门参观游览。 资料图
故宫太和门构图比例分析。 王南配图
“中国古建筑有很旧甚至很破的,但几乎没有丑的。不用特别多的雕饰,哪怕是极普通的一间小房子,看上去也是美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横在面前的是一个回荡了几十年的问题: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古典建筑遵循“黄金分割比”一样,也有对美的比例的追求吗?
事实上,对中国古建筑美的密码的追寻,由中国营造学社先辈们肇始,历经梁思成、林徽因、陈明达、傅熹年、王其亨等,八十余年来几乎从未停止。
“经过几代学人的持续研究,今天我们可以说,答案是肯定的。”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王南说。
没有等待太久,2024年5月,王南的论文《天地圆方 塔像合一——应县木塔建筑空间、塑像群与壁画之构图比例及尺度探析》将在《Religions》——一本A&HCI期刊上发表,后者被称为艺术与人文领域的SCI。
“这是一项非常原创的研究课题。”一位专家的评审意见写道。
论文的核心,是这位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基于方圆作图的构图比例,特别是和是中国古人在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建筑设计中,广为运用的重要比例。
这是此项发现第一次系统地呈现在英文期刊上。新声音回答的是一个老问题:西方古典建筑有着严格的对美的比例的追求,被建筑师、艺术家奉为圭臬的“黄金分割比”就是代表。有着数千年营造史的中国呢?
“经过几代学人的持续研究,今天我们可以说,答案是肯定的。”王南说。
作答的过程不乏跌宕和巧合,但如果把目光移远一点,不难看到数十年来几代学者的接力,数百年来无数匠人的传承,数千年来一个文明和她的宇宙观的延续。
更重要的也许是,这在回答历史,也在回答未来——我们如何创造一座美的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有对美的比例的追求吗?
看过无数古建,令王南印象极深的,是一座寺院不起眼的一隅。
那是北京香山的碧云寺。2012年他们前去测绘,中午时分,几人绕到前院廊庑的转角处休息。那里远离中心大殿,只是回廊的转角,同行的友人突然感叹,“都到这儿了,一眼望去,照样那么美!”
这句话王南记到现在。“中国古建筑有很旧甚至很破的,但几乎没有丑的。不用特别多的雕饰,哪怕是极普通的一间小房子,看上去也是美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时,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他正参与一套古建筑丛书的撰写,想着“怎么也得画些漂亮的古建筑测绘图放到书里”,他拿起了测绘工具。
测到北京五塔寺那天,正赶上雾霾,全站仪一直报错,王南准备第二天再校核一遍。没想到,两天的总高数值竟然差了一米多。按校正后的数据计算,他发现,五塔寺金刚宝座塔的整体高宽比是7:5。
这次阴差阳错,让王南第一次对“一座中国古代建筑的整体高宽比是个完美的整数比”有了深刻的印象。
但一切差点停在了这里。
横在面前的是一个回荡了几十年的问题:中国古代建筑,有对美的比例的追求吗?
1980年,在清华大学读建筑史的王贵祥跟随老师、著名建筑历史学家莫宗江去福州测绘华林寺。画测绘图时,王贵祥注意到一组数——从剖面看,地面中心到两侧的橑檐方,和到脊槫上皮的距离是一样的,这在之前的报告中没写过,他联想到了半圆。紧接着他又发现,殿内内柱上的中平槫上皮高是内柱柱顶高的1.41倍,他马上想到了圆和方——正方形外接圆的直径是正方形边长的倍(约等于1.414)——这是不是刻意的?
不久后,王贵祥又跟随莫宗江测绘了杭州闸口白塔。回到北京画塔身外檐剖面图时,莫宗江发现其檐高与柱高之间也存在1.41倍的关系,他兴奋地把王贵祥叫过去说,你是对的。
很快,在研究了独乐寺山门、南禅寺等20多座唐宋木构建筑之后,王贵祥发现,在檐高与柱高、通面阔与通进深、明间面阔与次间面阔等不同方面,都存在着构图比例。他将这个比例和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联系了起来。
“古人并不一定理解这个无理数,但从圆和方的关系中得到了对这个数理的认识,而且画方画圆很容易得到。”他认为,使用这个比例和追求美的视觉效果有关,可以使两部分“既有了较明确的关系,又有了恰当的过渡,造成所谓‘不即不离’的视觉效果”。
可没过多久,提醒就接踵而至。有人告诉他,“这个东西欧洲人研究了几百年,你千万别碰,碰这个东西是没有结果的。”
加之那时资料和数据很难获得,研究不得不搁置。他在一篇论文的结尾写道,“(这个比例)在唐、宋时期,不仅在单檐建筑中,而且在楼阁或塔幢建筑中也可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由唐、宋时代向前追溯至秦、汉,或向后下延至明、清,是否也可能发现类似或相关的比例处理规律,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有待学界同仁的继续努力。”
几年后,正在攻读博士的王南,看到了已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的王贵祥的研究,第一反应是将信将疑——“总觉得这是属于西方人的东西,好像中国人不该有这种基因。”
即便自己测绘发现了五塔寺金刚宝座塔的比例,他还是心存疑虑。“被自己长期以来的偏见误导了。因为金刚宝座塔是印度来的,我们就觉得,看来印度建筑和西方建筑一样,也很重视比例。不太相信中国古代匠人会这样干事。”
无处不在的“天地之和比”
所幸来自五塔寺的启示太过深刻。抱着试试的想法,王南又测绘了几处古建筑,发现总轮廓尺寸竟然全都存在清晰的比例关系。
这出乎了他的意料。等不及逐个测绘,他找来公开发表的测绘资料,一头扎了进去。本来想做的其他题目通通舍掉,答应出版社的几本书也搁置了,他觉得这是“头等大事”。“即使证明不对也行,那就说明中国古代匠人确实没有对经典比例的追求,这也是个重要的科学的结论。”
没想到,发现的构图比例越来越多,7:5,10:7,6:7,7:8,3:2……还有大量难以取到整数的比例。研究快两年时,他跟朋友做了一次内部研讨,大家觉得案例不少,比例也不少——问题是,统领这些比例的规律究竟是什么?
那天晚上,王南彻底失眠了。辗转反侧间,他突然想起白天有位学者无意间提到圆规。“我之前一直通过画矩形来研究比例,从没往圆形想过。回头重新思考王贵祥老师提出的比例,就是圆和方的关系。”第二天,他和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谈到自己的想法,两人在咖啡馆的纸巾上画方圆草图,越画越觉得,“这很可能是那一系列比例的根本”。
是正方形与其外接圆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古人简化为整数比7:5或10:7(7:5=1.4;10:7≈1.428),“方五斜七”的匠人口诀流传至今。同时,以正方形相邻两角为圆心、边长为半径分别作圆,交点相连,能得到等边三角形,包含这个等边三角形的矩形,短边与长边之比为,同样被古人以整数比6:7或7:8替代。这样的矩形构图,时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王树声2009年在对隋唐长安城平面规划的研究中已经发现。
这一下,之前很多悬而未决的比例数字不“悬”了。王南决定,把积累的几百个案例依照新思路重算一遍。结果,、像“洪水一样”涌了出来。
比如故宫的三大殿,既存在构图比例,又存在构图比例。又如国内最重要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高宽比为1:2。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比值,恰好是世界现存最大的木构佛塔应县木塔的宽高比——两个国宝的构图,正好转了90度。
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的一项研究吸引了王南的注意。在距今五千多年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出一组圜丘和方丘,冯时研究发现,祭天圜丘是以三重圆坛表示夏至冬至春分秋分的日行轨道,三个同心圆的直径由内到外分别为11米、15.6米、22米,呈倍数关系。
在此之前,王南分析的最早案例是汉长安城,牛河梁遗址较之提前了3000多年,这让他始料未及。“如饥似渴”地搜集考古报告、一路捋下来后,他发现,从偃师二里头,到岐山凤雏西周礼制建筑遗址,“一些早期看似不甚规整的建筑遗址,都在运用这些比例”。
眼看案例越来越多,可最后一槌还是迟迟难落。科学的论证需要实例和文献二重证据,换句话说,推测得对不对,还需古人的“证词”,后者却一直未现。
北宋《营造法式》“圜方方圜图”。 王南供图
一筹莫展时,他“鬼使神差”地从书架上摸出一本北宋《营造法式》的图版,随手一翻,第一张图赫然就是表现圆方相接与相切的“圆方方圆图”。这本中国现存最重要的古代建筑专书,还引用了更古老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周髀算经》的一段话:“万物周事而圆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
梁思成所作的《〈营造法式〉注释》王南读过很多遍,并没在正文中见过“圆方方圆图”,后来才知道,为了给研究者以方便,梁思成将原书很多插图重绘为现代工程图纸,偏偏这最为重要的第一幅插图,由于历史原因未及重绘,原图则被收进了附录。“《营造法式》原书中,它是第一张图,在‘总论’部分,‘总论’又是读懂整个法式的核心。”王南说,“这样看来,基于方圆作图的构图比例对于中国古建筑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在王军的启发下,王南将这套构图比例称为“天地之和比”。2018年底,《规矩方圆,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下称《比例研究》)出版。书中写道:中国古代匠师广为运用的基于方圆作图的构图比例,蕴含着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与追求天地和谐的文化理念,可谓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中源远流长的重要传统。
这本书收录的400多个实例,在地域分布上,遍及北京、河北、河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建筑类型上,涵盖了中国古建筑的绝大部分类型。王南以汉代举例:最大的案例汉长安城遗址,城垣内面积36平方公里;最小的案例孝堂山墓祠只比人高一点,“所用的比例手法竟是一模一样的”。
在时间跨度上,从新石器时代贯穿至清末。牛河梁圜丘的三个同心圆,在故宫千秋亭的平、剖面上重现;唐代佛光寺东大殿1:2的高宽比,与清光绪时期重建的故宫太和门如出一辙。
“一以贯之,一以贯之,一以贯之。”王南重复了三遍。
接力破译90多年的“密码本”
“你看这些,全是密码本。”
站在故宫熙攘的人群中,王南指着太和门和周围的建筑。“你看到的是一栋栋房子,它们不会说话,但背后的秘密全藏在身上。我们的工作就是解锁,通过研究让它们说话。”
如果把中国古建筑沉默的千年比作一天,让它们开口说话,在最后一小时才开始。
《比例研究》开篇写道,“本研究可谓是对一个老课题的新发现。所谓老课题,即对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规划设计方法的研究,尤其是规划设计中的构图比例问题的研究。此方面研究由中国营造学社先辈们肇始,八十余年来几乎从未停止。”
20世纪初,英国学者弗莱彻主编的《比较建筑史》里著名的“建筑之树”,将西方建筑作为主干,认为中国建筑不过是一个“非历史”的次要分枝。这样的偏见时人却无力反驳。在这之前,中国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建筑技艺主要靠工匠口传。中国建筑患上“失语症”。
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规律到底是什么?
率先作答的是日本和欧洲学者,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在《支那建筑史》中断言:“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这个局面被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和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学社同仁的急起直追打破。国家民族存亡的关口,他们希望科学地、系统地阐释作为“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的中国建筑的独特价值。
构图比例的研究,是其中一条主线。林徽因曾特别谈到建筑比例权衡的重要性:“至于论建筑上的美,浅而易见的,当然是其轮廓、色彩、材质等,但美的大部分精神所在,却蕴于其权衡之中;长与短之比,平面上各大小部分之分配,立体上各体积各部分之轻重均等,所谓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玄妙。”
翻开破译了90多年的“密码本”:梁思成林徽因对宋式、清式建筑“模数制”的发现,初步确立了单体建筑的比例权衡之法;建筑学家陈明达对一座单体建筑的构图比例及设计方法进行全面剖析,开研究之新风;傅熹年、王其亨等学者进一步发现,不仅单体建筑,建筑群的外部空间,包括园林与城市,皆运用模数格网加以规划设计……
“古人用材、方格网为度量单位。这个单位是怎么设计的?取什么数?王贵祥、王南等学者对比例的研究,回答了这个层面的问题。”长期研究中国古代规划及宫廷制度的王军解释道,“这样一种设计方法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观念,直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虽然一度遭到遗忘,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前赴后继,我们终于把她找回来了。”
“一个成果真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王贵祥说。
几年前,王南把书房名从“意象斋”改成了“执矩斋”,他说这是自己学术研究的一次分野——由定性转向定量。“数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可能真的被严重低估了。我们长期缺乏对中国建筑中数学、美与建造之间密切关系的认识,甚至误认为古代匠人是蒙着干活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人恰恰有着重视建筑比例的悠久传统。”
某种程度上,对这个传统的追寻,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古代城市、建筑之美的一道数学证明。
就像碧云寺一角给王南带来的冲击,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埃德蒙·N·培根也被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击中了。这位曾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规划师,在著作《城市设计》里高度赞美北京的规划设计呈现出“从一种比例到另一种比例的流动”:“北京古城的规划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规划,它可以从一种比例放大到另一种比例,并且任何比例都能在总体设计方面自成一体。”
翻开《比例研究》中对北京城的分析图,指着此起彼伏、层层嵌套的圆和方,王南说,“从城市到建筑群再到建筑,反复使用同一套方圆作图比例,这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培根感受的根源。”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宗教建筑与其中的塑像、壁画之间也存在比例关系。“你在中国古建空间里感受到的和谐是全方位的,甚至里面的塑像、壁画乃至器物,所有东西在共同起作用。就像音乐,音阶加上节奏、韵律,整体和谐之感流动了起来。”王南说,即将发表的应县木塔论文就是对此的一次综合诠释。
应县木塔(资料照片)。应县木塔建于辽代清宁二年,即公元1056年,距今有955年的历史,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建筑。新华社发(李文魁摄)
“中国古典的比例与西方的黄金分割比例,实际上都基于人类的某一种基因,这种基因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智慧,就是你画到这,大家都觉得好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说。
器以载道
不过,在王南看来,美可能还不是这个比例“最核心的内容”。
“在远古时代,能盖房子是件大事。建筑其实是一种纪念碑,一个文明会把至关重要的事情刻在上头。”王南认为,方圆作图比例,就是一个农耕民族“刻”在建筑中的宇宙观。
“我们可以认为‘天圆地方’是古人以为的宇宙模式,更可以认为‘天圆地方’是古人测量天地、观象授时的方法。”王军说。
他解释,掌握时间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前提,中国古人发展出一套观测时空的方法——在一个圆周里通过天文观测获得时间,在一个矩网里“计里画方”测量大地。在这样的实践中,古人形成了关于方和圆等空间布局的传统思想,考古发现可追溯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圜丘和方丘。
他认为,或许应从这个角度理解“万物周事而圆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因为读不出时间与空间就无法产生农业,无法做到‘万物周事’,更无法迈入文明的门槛。我想,这就是‘天圆地方’最重要的意义,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定义了我们的文明。”
“方圆合即天地合,天地合即阴阳合,‘阴阳和合而万物生’。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支撑农耕文明的观象授时知识体系,中华先人对万物生养的哲学思考,正是通过这样的图式直接呈现,中国经典的美学比例导源于此。”他说。
冯时指出,近年考古发现红山文化的另一个圜丘,三圆比例呈现等差数列的关系。“中国古代建筑的法式除了‘方圆做图’所涉及的比例这一种,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式?”他认为研究可以继续深入下去。
眼下,王南把目光投向了青铜器,尝试挖掘其中“蕴藏着的文明密码”。他发现,经典比例不仅存在于古代建筑和城市之中。
“这些研究都在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文明源头的重要知识体系如何在器物中得到呈现,如何‘器以载道’。”在王南看来,研究这些并不是要证明我们的文明优于别的文明,而是试图揭示中国古人,或者说人类有过这样一种宇宙观。尽管“天圆地方”的宇宙空间观念早已远去,但追求人与自然、宇宙和谐相处仍是不变的主题。
每次有新发现,他都有个冲动——向古人三鞠躬。他认为,“中国古人只会比我们目前所能设想的更加富于智慧。”
几代学人的接力,让这些智慧正慢慢重现。“前辈们的研究,已经使中国建筑史特立独行于世界建筑史之林。科学的系统的,可以与世界建筑史学对话的学术路径,已经初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王贵祥说。
那幅“建筑之树”早已从《比较建筑史》里拿掉,几年前,《比较建筑史》的编辑找到王贵祥,希望使用一项他关于中国建筑的研究成果。“中国建筑思想正在世界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
《比例研究》出版的那年夏天,王南去日本东京大学做了一次学术报告。在对日本最重要的一批佛塔进行研究后,他发现,绝大多数塔的总高与塔刹以下高度的比值都是。“这套比例手法其实也影响了日本。”
听完他的报告,日本建筑史学者藤井惠介回应道,很遗憾,现在日本学界不太做这方面研究了,反而是做维修保护的工程人员更关注这些,日本学者也应该把这项研究重新捡起来。
“中国人来研究他们的了”,王南感觉到,这促使日本学者“重新审视自己”。
“过去我们一直要努力证明我们也有自己的建筑史,也有属于自己的经典建筑比例,现在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了。西方有着以黄金分割比为代表的经典比例,这套经典比例是不是从新石器时代直到近代,从城市规划到单体建筑都能一以贯之地运用?是否也有一种传承不绝的宇宙观和文化内涵蕴含其中?现在,这些问题抛回给西方学者了。”王南说。
新一代之成规
2024年3月,“三山五园园林艺术传承与数字再生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课程过半,项目负责人、北京理工大学长聘副教授严雨给学员布置了一项作业:在一块42米×30米,也就是长宽比近似的场地上设计一座园林。
他这样解释作业的目的:“引导学员探寻在设计当中的应用,变成一种自觉。”
怎样在传统和现代间搭一座桥,是这位建筑史学者一直琢磨的问题——从事了多年建筑设计和建筑学教学后,他选择重回学校,研究中国建筑史。
“我们在学校里学建筑学,在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延续的都是西方建立的建筑学体系。做建筑设计,我们会推敲比例,自觉运用黄金分割比,也会去推敲帕特农神庙。但我们没去分析自己的紫禁城、天坛。我们不知道中国自己竟然有一套经典比例的密码。这个研究为我们今天建立中国建筑文化自信和构筑中国建筑学体系树立了信心。”严雨说。
在一次《比例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上,时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的庄惟敏提到了相似的话题,“我们很多学生,包括中青年建筑师,也在用中国的建筑‘武装’自己,可是他们的‘武装’实际上是一种符号化的东西,就是试着带点中国传统的元素,却没有真正掌握里面的精髓。”
这场研讨会上,900多年前《营造法式》编纂者李诫的一句话被反复提起:“非有治三宫之精识,岂能新一代之成规?”
在“治三宫之精识”不断重现的今天,很多人也感到让“精识”走出去的紧迫——“千城一面”“缺乏中国特色”“奇葩建筑”的公众评价,凸显着现代中国建筑面临的困境。
“我们能不能在建筑史学的基础上‘新一代之成规’?这已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王南直言,“有人认为要创新就必须抛弃传统,还有些设计者不屑于去受一些规矩的束缚,觉得这样影响了他的创造力。”
这个问题在80年前已有回应。1944年,抗战尚未结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停刊7年后艰难复刊,梁思成以《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开篇。
他写道,“无疑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古人的经典是大浪淘沙的产物,照着美的规律做,首先不会出错。”王南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当代城市与建筑新的“规矩”,不但不会限制创新,反而会成为自由创作的基础。
“将来我们有些建筑的设计是不是也可以运用这样的方法?”研讨会上,崔愷问道。
他建议,“这应该作为中国建筑教育非常重要的课程。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们,不管他们是不是很聪明,是不是很有天赋,都能很清晰地认知甚至掌握这种方法。这样,中国建筑的形式美和总体上的美学水平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方圆作图比例正成为严雨课上必讲的内容,在他的建议下,“三山五园园林艺术传承与数字再生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名字里,特意用了“再生”二字。
“所谓再生,不是形式简单做复制,是一种基因在传承。”
布置完的作业,这位老师告诉年轻的学员们:“中国建筑核心的文化艺术基因,这是不变的,是我们应该发掘和继承的。最终,就如梁思成先生所说,雄厚我们的创造力量,创造我们自己的建筑。”(记者徐欧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