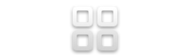开往北大荒的列车
王秋和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出发,当时是下午四点半。十多分钟后就到了丰台火车站,我和同学们正在想着再看一看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趟专列竟然停下了。
已经在车站等候多时的人们人山人海,他们看到火车停下来,就像潮水般呼啦啦地涌过来,将列车团团围住。“潮水”中的声浪里,都是呼唤着的亲人名字,这阵势和刚才永定门火车站的悲壮情景如出一辙。
原来,我们知青中有不少人是铁路职工子弟,他们的亲人知道这趟知青专列要去东北方向,丰台火车站是必经之路,况且火车要在这里加水。
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知青的家长们几乎都知道了,纷纷跑到丰台火车站来想再见自己孩子一面。
望着黑压压的人群,我不禁惊得目瞪口呆,这场面太壮观了。我猛然看见同班同学曹闻的父亲正在四处张望,他突然看见了我,并努力朝我们这个窗口挤过来,嘴里还在呼喊着什么话。
我根本听不清他在讲什么,但是我通过他的口型知道了大概意思,肯定是询问他的儿子在哪节车厢里。
我忙回头将曹闻叫过来,这个曹闻长得胖乎乎的,却像一只小螳螂般灵巧。他赶紧挤到我刚给他让出窗口边上的最好位置,与他父亲话别。
我挤在窗口的另一角焦急地四处寻找我的亲人,希望他们能到火车站来。因为下午在学校送行时,由于太激动,还有很多话忘了讲。
这时每个车窗前都挤着十几张十五六岁的娃娃脸,就像十几棵正在往上蹿的向日葵般挤在了一堆,拼命要争抢阳光一样,都在争先恐后地想把小脸露出来。
同学之间这时候谁也顾不上谦让,都只顾自己和亲人依依惜别,个个热泪盈眶,声音悲悲切切。我已经被挤到了第二层,就索性站起来,透过车窗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亲人。
突然,我发现父母就站在不远的站台边上,焦急地在巡视着车窗上的一个个小脸,希望从中看到自己的儿子。
家里人从学校来到火车站等我,只为再看我一眼,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家没有人在铁路部门工作。我心里头激动惊讶、喜出望外,很难说清楚的多种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我忙弯下身子,用头拱了拱曹闻的头说:“你快点和你爸说,我爸妈也来了。”曹闻的头往旁边挤了挤,另一边上的人头碰在车窗框上,一边吸冷气,一边叫“轻点”!
我扯着嗓子大喊:“爸爸,妈妈……”我发现,不光我在喊这两个词,很多车上的知青都在喊这两个词,展台上的爸爸妈妈太多了,分不清是不是在叫自己。
我听说人最独特的地方是声音和走路姿势,每个人都是独一款。我的亲人终于在这么多的“爸爸妈妈”声中,辨别出了我的声音,他们扭过脸发现了我。弟弟妹妹也看见了我,便朝我这个窗口挤过来。
站台上的人实在太多了,爸爸和妈妈离我虽然只有十多米远,却挤了十多分钟。弟弟妹妹由于个子矮,被淹没在如潮的人海中。我偶尔看见他们在大人们的肩膀后面露一下头,看看我,然后又钻进“潮水”里去,朝着我的这个窗口“潜水”过来了。
我不再喊叫了,因为怎么喊叫也是徒劳的。这列火车从水定门出发时就让人们流了不少眼泪,既然它连眼泪都不相信,怎么会相信喊叫呢?
火车一阵一阵的鸣着笛,企图干扰人们的哭声,让人们躲开,表示自己要走了,却也是没人听,仍然寸步难行。
爸爸妈妈也不再喊,只顾同挡在前边的人大声而客气地说:“劳驾,对不起,让一让……“
我看见爸爸一向梳理得很整齐的发型有些凌乱,妈妈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晶莹发光。
我这个是时候才猛然觉得,他们的心里其实是不愿意让我离开家,不仅我还不到十六岁,似乎我也不应该离开他们。
可是我转念一想,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没有错,不经风雨见世面,怎么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况且半年多前,甘肃会宁县有些人提出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如果我们不上山下乡,是不是就要在城市里吃闲饭了……
爸爸妈妈终于挤到了车窗前。妈妈心疼地对我说:“你中午走的时候,也忘了给你带上个水壶,我们刚才给你买了个大西瓜,你和同学们在路上一块吃吧。”说着,将一个大西瓜递上来。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他们朝我这里挤得这么慢呢,除了人多拥挤外,原来他们手里还拎着一个大西瓜呢。
我顿时有些于心不忍,连忙说:“我带着杯子呢,你们还买西瓜来,太费事了嘛!”
正说着,妈妈的西瓜已经举上来了,我急忙伸手去接。可是这个西瓜太大、太重,车窗距地面太高,她刚举到胸前就有点力不从心,而我刚能摸着西瓜。
这时爸爸的一双大手从下面一托,将西瓜举到了窗口,对我说:“赶快接住,你妈都快举不动了……”
我急忙将半个身子探出车窗双手接住,这西瓜确实够重的,恐怕是市场上最大的西瓜了,我将它抱进来放到茶几上。
我这时想和爸爸妈妈多说几句话,可是我突然看到妈妈发红的眼圈,便只叫了一声:“爸!妈!”便有点哽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大滴大滴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视线也有些模糊了。
妈妈慈祥的目光望着我,她似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儿子就要远离父母,到刚刚发生过“珍宝岛事件”的中苏边境去戍边,是福是祸?
还不到十六岁的年纪和八十多斤的体重,要是受到同学欺负,打架都吃亏。现在却要去打仗,还是和人高马大的外国鬼子打仗,打得过敌人吗?
再说东北那么冷,能受得了吗?想到这些,妈妈便开始尽量用大声地叮嘱我:“天冷时要注意穿厚一些,千万别冻着自己……需要什么东西就来信……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和同学们搞好团结,别闹意见打架……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当个好战士,要求进步……”
我的心里很难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不住地点着头,嘴里“嗯、嗯”地答应着。渐渐地,妈妈的话音开始有些哽咽,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但她的嘴角依旧蠕动着,不停地将说过的一件事、一番话,断断续续地、又反复嘱咐着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此刻也说不出什么,只有不住地点着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脸颊流下来,“啪嗒啪嗒”掉落在车窗外面。
此时,我突然看到妈妈后边站着的爸爸,他侧着脸在认真地倾听着妈妈嘱咐我,他手拿一把纸质折扇,下意识地轻轻扇着,似乎很悠闲。天气已经不是很热了,折扇就好似他手中的一件道具,偶尔扇几下,又折起。但他眼睛却冷静地巡视着周围的人山人海,对“山海”中那沸腾的气氛似乎又熟视无睹。
一向很坚强的爸爸若有所思,却始终没有对我说一句话,但他站在那里,我就感到像有了靠山一样。
我突然觉得应该像爸爸一样坚强,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的意志起不到一道堤坝的作用,无法阻挡自己眼中往外涌出的泪水。
爸爸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也很严厉,他不是一位靠说儿女情长语言来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但我从他那刚毅的眼神中,已经读懂了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这时弟弟妹妹也挤了过来,他们仰着脖子惊讶地看着哽咽的我,又看看还在嘱咐我的妈妈,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们以前没见过妈妈这么伤心地流泪,也没见过周围这么多人都在毫无顾忌地痛哭流涕。
面对这一切,我拉着妈妈的手,哭不出声音,只有抽泣,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安慰她……
这让我后悔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这次分别时没有将一个非常坚强的形象留在亲人们的眼中,而是留下一个哭哭啼啼的、懦弱娇气的样子,让他们为我担心和挂念。
可是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真实感情的流露,故作坚强的样子是无论如何也装不出来的。我后来常常想,是谁面对这种痛哭的场景能够无动于衷?没经历过“暴风骤雨”的人恐怕不可能有。
这时,很多知青的亲朋好友都用手扒着车窗或与车上人拉着手,列车司机根本不敢开车。车站的广播中不断地重复着播音,火车马上就要开了,警告送行的人们离开车厢一米远,站在安全线外面。
列车员和车上送行的老师反复地对知青讲,要把头和手收回到车窗内,可是所有送行的和远行的人都把他们的话当成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直到丰台火车站上的很多执勤人员都跑过来维持秩序,连拉带拽地劝解着送行的人们。列车不失时机地拉响了最高分贝的汽笛声,这声音盖过了车站所有的声响,送行的人呼啦一下闪开了,我们的手也急忙松开了。
列车吼叫一声,“咣当“一声,终于启动了。随之而起的是一片哭声似旋风般响起来,车窗内外数千人的哭声交汇到一起,震耳欲聋,排山倒海,宏大场面空前绝后……
我说空前绝后真是没有一点夸张,因为在此前和以后,我始终没有见过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和哭声。直到现在,我只要一想到这个送别场景,仍然禁不住心要颤抖。
我想,只要是有感情的人,面对此情此景,都不会无动于衷,这是一种面对骨肉分离而又无可奈何的悲情场景。作为家长们,不知孩子此去将会怎么样,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甚至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回来。
事实上,后来确实有同班同学(战友)献身于北大荒,也有很多同学带着一身伤病返回了城市。这种事以后再详细说。
当时毕竟上山下乡的孩子当时还太小,毕竟还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更没有任何社会经验,毕竟是太小的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就要走得这么远。大家痛哭就是这些感情汇集到一起后最好的发泄方式,是一种控制不住感情流露。
所以说哭并不一定是人的性格懦弱的表现,有时也是坚强的人用以表达自己性格中的一种坚强而已。
因此可以说,哭也是某些人的另一种坚强,不哭的人只是感情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是不是心里在滴泪,不得而知。
火车是不管哭声大小的,它只顾自己“咣当咣当”地往前走。车厢外的哭声被远远地甩到了后面,很快就听不见了。
车厢里的哭声没有了外面的呼应,也变得单调了,开始越来越弱,逐渐变成了抽泣声。渐渐地抽泣声也越来越弱,越来越单调,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此时,列车车轮碾压在铁轨上而发出的那种单调的、有节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行走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越来越急。
突然有人说:“啊!廊坊到了。”
有人打开车窗,呼呼的风灌了进来,同学们的抽泣声越来越小,听不到了,整个车厢出奇的安静,安静得有些瘆人。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人人都是若有所思,个个都在发愣呆坐。车厢里显得死气沉沉,透着一种压抑,一种难以忍受的枯燥和单调。车厢里面仿佛是一堆没有灵性的货物。
这时,受学校委托,送我们到目的地的刘老师站起来说:“大家别这么闷闷不乐的,咱们一起唱个歌活跃一下气氛吧,我打拍子。”他用手扶了扶眼镜,便没放下来,而是做好了打拍子的准备,就像双手端着一盆空气的样子。
刘老师的热情提议受到冷遇,大家似乎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他也不在乎大家的反应,继续说:“咱们马上就是兵团战士了,一起唱个《我是一个兵》吧。”
刘老师说完,也没顾得看看大家的反映,就自顾自地领唱道:“我是一个兵,预备--唱!”他随着自己的歌声挥舞起手臂唱起来。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他刚唱了两句,突然发现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单调声音在独唱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放下刚刚舞到空中的双手不满地说:“你们怎么回事啊?要唱大家一块唱。”
听刘老师那口气,他似乎还以为是在学校的教室里指挥学生们唱歌。他没想到面对的学生已经是兵团战士了,角色转变,不受他领导了。
知青中突然有一个人阴阳怪气地说:“我们不想唱!我们想下车,我们想回家--”这拉着长声的回答,顿时激起一片七零八落的嘲笑声。是嘲笑老师,还是嘲笑这个阴阳怪气的同学,不得而知。
说这话的人正是一贯调皮捣蛋的“豹子头”。这个平时在学校就表现得流里流气的淘气学生,还经常和社会上的一些小流氓在一起打架斗殴,甚至动不动就玩刀子,基本上无人敢惹。
这个家伙长得脏兮兮的,头发乱糟糟的像个鸡窝,有同学背地里送了他个外号“豹子头”。他开始对这个外号很反感,谁敢叫,他就跟谁急。后来他听别人说这是水浒英雄林冲的雅号,就笑纳了。
可是这个家伙却不会仗义行侠,却常常横行霸道欺负瘦弱的同学。兵团怎么能要这样的人呢,我们中有这样的人同行,今后的路上我们不光要与天奋斗、与地奋斗,还要与人奋斗。
这些“人”里除了苏修侵略者,还包括知青中调皮捣蛋的人。想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一紧,真是任重道远啊……
刘老师一看是“豹子头”故意挑头捣乱,他久闻其恶名,便也没了脾气。于是自找台阶下,尴尬地笑笑说:“我看大家好像累了,先歇会儿再唱歌吧。”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