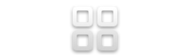北大上学时的社会实践及联想
王秋和
考上大学学什么专业固然重要,但与以后从事什么性质的工作未必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有一点是必须的,就是都离不开社会实践。因为一切真知灼见或在事业发展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我们在北大中文系上学的时候,对社会实践比较重视。
①中文系建系百年时
记得我们班同学曾经到定陵考察实践,到荣宝斋的木刻水印作坊学习实践,到国子监处的首都图书馆、到文津街北侧的北京图书馆学习整理善本书目实践,还在北京汽车制造厂的职工宿舍住了三个多月,师生同吃同住,与工人们同劳动同学习,共同搞展览和社会实践……这些社会实践对学生们的成长和发展是非常重要和十分必要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庆祝会的时候,我们班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大多回校参加纪念活动。在当年的学一食堂(后来改建成了北大百年大讲堂)开大会,各年级师生来了不少,用座无虚席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这次中文系系庆在大讲堂的醒目位置挂出了一些意义深远、文采飞扬、甚至散发着古色古香气息的楹联,颇能体现中文系的特点与师生们的情怀,其中有一幅楹联写的是:
阐自由之精义,昌明学术,百年风雅同歌咏;
济苍生而文章,陶铸人才,今代学林称典型。
这次在大讲堂召开的大会上,著名作家刘震云作为已经毕业的学生代表登台发言,他当时说到的一句话可谓振聋发聩:“我刚入学的时候,中文系杨晦主任就对我们说,‘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一个作家上不上北大中文系,决定了他的路能否走得更长,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段话赢得了北大百年大讲堂内中文系师生们热烈的掌声和由衷的笑声,刘震云面对这种情况,左移了两步,向着台下的听众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刘震云的这段话之所以引起在场人的共鸣,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本身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又是一位当代文坛有成就、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比较“长”的著名作家。也因为如此,他补充说自己“有悖于老师的教诲”,这就完全是幽默之语了。杨晦先生给我们讲过课,我以为,杨晦先生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我们上学时的北大中文系有文学专业,还有新闻专业,汉语专业;我们班是古典文献专业有点特殊,属于隔年招生,全班只有17名学生、14位老师(教授)。
中文系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后来“学非所用”的不在少数,我们班同学也是如此,当老师、做出版、搞新闻、进行医学研究或古籍研究的都有。
其实,上大学就是为学生们将来自立于社会打下一个基础,让学生掌握更多更好的学习方法,至于学生毕业以后做什么工作,从事什么专业,那就要看他的兴趣、造化和机遇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从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应该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和文字表达功夫。
②意义的社会实践
我大学读书时也做过作家梦,记得有一次学校布置我们班里同学常振国、高路明、杜文彬和我到北京大兴县魏善庄公社河南辛庄大队搞社会实践,与村里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们是随大兴县工作队一起进驻这个村子的,他们工作队的任务是整顿和组建村子的新领导班子,我们每个同学这期间的学习任务就是要完成一篇论文。
高路明写的论文是篇人物通讯,记述刚刚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石景发在逆境中如何成长的事迹。工作队长要求高同学在村党支部大会上念这篇人物通讯,向大家征求意见。
参加征求意见会议的还有县里驻村工作队全体成员,工作队队长就是县武装部的部长,一位部队转业干部,个子虽然不高,但嗓门洪亮,一看就知道他经常在大庭广众前面鼓动或训话,他说话干脆利索,决策事情一锤定音。
高同学的文章带有一种文学色彩,她念稿子的时候带有一种感情色彩,语调抑扬顿挫。屋子里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静静听着,除了高同学的声音,没有任何杂音。
这篇写真实人物的稿子确实好,用词准确,生动形象,真实感人,文字朴实又文采飞扬,我自愧不如。心里却在想,我也整天和石景发接触,高同学写的那些事我也知道,怎么就写不出这么感动人的稿子呢……
当时,憨厚朴实的石景发闷头坐在土炕的炕沿上,我坐在他对面一个矮柜子上。我看到石景发听着听着就渐渐低下了头,双手捂着脸颊和太阳穴的部分,让人看不到他的面目表情。我以为,高同学正在读的稿子就是写他的,当事人觉得不好意思是正常的,我也把眼神移开,不再看他的表情了。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渐渐地我听到了一种水滴掉落到布面上的轻微声音。我抬头一看,只见石景发间或还发出小声的唏嘘,双手没有捂住的脸颊下边流出了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他的膝盖上,把他的裤子打湿了,水滴声音的制造者就是他的眼泪掉落在裤子上面传出来的。
石景发当时年近四十岁,是位五大三粗的庄稼汉啊!男儿有泪不轻弹,他的眼泪是对高同学这篇作品的肯定和感动,因为文章写到他心里去了,挖掘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石景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说不出多少表白自己或感谢他人的话,但我的同学却用文字的魅力和文学的感染力让他控制不住感情,导致泪流满面。
高同学念完稿子之后,武装部长带头使劲鼓掌,一个劲说高路明的稿子写得好,连连夸赞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不简单……我们所有在场听的人都深受高同学这篇作品的感染,一致称赞写得好。
严格说,高同学所写的这篇稿子是带有文学色彩的人物特写,按现在的分类似乎属于一篇报告文学或者说是纪实文学。因为写的是真人真事,融进了真情实感,且具有文学色彩。
我当时就觉得,高同学将来或许能够成为一位作家。写出感人肺腑的好文章并不容易,需要有点文学功底和扎实的文字基本功,那样写出的文章或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震撼力是不容低估的。
若干年之后,我们班同学聚会时,我见到高路明同学,与她说起此事。她说当时只顾得念稿子,没注意别人的反应……高路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现在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述颇丰。
我们上学的时候,班里同学大多很年轻,班里显得老气横秋的是两位三十岁出头的湖南同学周同钧和江苏同学吴国兴。这两位老同学毕业后回了原籍,从此就与我们班所有同学失联了,说起来挺遗憾的,因为那是两位很朴实的老同学,其中的周同学甚至有些土,土的有些掉“渣”。
由此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年龄代沟有时也就十岁左右的宽度或深度,这在人生二三十岁的时候就逐渐形成了,只是有些人在那个年龄阶段还没有感觉到而已。
③年学生喜欢写诗
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年轻人大多有一个普遍爱好--写诗,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现象,尤其是大学生更是如此。
首先是年轻人对生活热爱,充满憧憬。这时对社会与自然的了解,对人类劳动与进步的追求,以及个人品质与社会中发生的不同现象和观念开始有新的认识与思考。在这种情形下,年轻人为了提升和改变客观现实和自己的追求,于是演变成诗歌,诗的语言最能表达年轻人的个人情感。
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在一首讽刺诗中曾经写道:“愤怒出诗作”。因为尤维纳利斯认为当时朝政腐败,道德堕落,用诗歌的形式针砭时弊最有力,即使没有写诗的天才,愤怒也可以产生诗作。
若干年后,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把“愤怒出诗作”修改为“愤怒出诗人”。其意义是解释一位平素沉默寡言、非常文静的同志出于革命热情而突然变得能言善辩、慷慨陈词的现象。就是说兴奋和快乐也能出诗人,那是因为情绪高涨,激情迸发,会化做一首首慷慨激昂的诗歌。
我们班很多同学当年也很喜欢写诗,甚至当时写大批判稿或大字报也是用诗歌形式写的。我们写的诗虽不太讲究格律,却也是很注意押韵的,读起来朗朗上口。
那时候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同学们写的决心书也有用诗歌的体裁,很能表达一种奋不顾身要去抗震救灾的冲动与激情。
同学们用诗的寓意和特点,把文字和语言锻造出来,把一腔热情变成一首首诗歌写出来。诗歌来源于学习、劳动和生活,也源于一种情感,其被当作一种生活中的爱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写诗是一种爱好,因为爱好,所以会希望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也会把人的精神变得更加充实。从而更加关注社会中一些事物的变化,包括对身边人和事更深入的了解和对人生意义的深度思考。
同学们写诗的时候,会有对人生的感悟和认知,来感受生活的馈赠,提升热爱生活的质素。我记得那时学校的大喇叭里经常播送关山先生用浑厚的声音朗诵长诗《雷锋之歌》,那是著名诗人贺敬之创作的,是当时风靡一时的优秀作品。
诗歌成为同学们的一大爱好,为了这一爱好,着实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有同学觉得写的诗歌怎么能够保留下来呢?如果不能保留,这些青春的印记岂不是被埋没了,是十分可惜的事情。
于是有同学主张编一本诗歌小册子,将大家写的诗歌收进去,这个主意马上得到同学们的积极响应。因为大家想起来《红岩》中革命者印刷的《挺进报》,那种油印的小报中蕴藏着火种。
有一段时间,晚饭后班里同学齐动手,刻蜡版,印刷、装订、设计封面,折腾了几个半夜,编辑出了一本不太厚的《萌芽诗集》,除自己留了一些外,还分送给系里的一些师生。
同学们捧着自己情感的结晶,劳动的成果,真有些爱不释手。此后的数十年中,我虽然搬了几次家,很多精装书都舍弃了,这本油印的诗集居然没有被扔掉,堪称奇迹,或者说是“硕果”仅存。
记得这《诗集》中有我写的一首小诗,当时被我们班辅导员汪圣铎看中,他在中文系的一次联欢晚会上朗诵了,竟然获得师生们不少掌声。其实诗歌写得很幼稚,主要是汪圣铎朗诵的嗓音很高亢,虽然略显沙哑,却富有感染力。
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那时正是我们中文系学生高红十和几位师生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广为传颂的时候,也是我们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年代,写文章或写诗的时候,难免蹦出几句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看着或听着都让人热血沸腾。
④谢所有的老师们
100多年来,从北大中文系走出来的文化名人实在太多了,以中文系主任为例,就有沈尹默、胡适、罗常培、朱自清、罗庸、魏建功、杨晦、季镇淮、严家炎、孙玉石、费振刚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从中文系走出的作家中就有陈建功、刘震云、曹文轩等等一大批人物,都已经蜚声文坛,获奖多多。当作家,是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文学青年最时髦的梦想,尤其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的梦想。
记得那时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很多,现在说起来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师,如王力、王瑶、游国恩、周祖谟、阴法鲁、梁柱、金开诚、严家炎、袁行霈、严绍璗、裘锡圭、谢冕、陈宏天、董洪利等等诸多先生,他们讲课的风格各具特色,至今印象深刻。
甚至当时在文艺领域颇负盛名的相声演员马季、作家浩然也来到中文系讲过课,不是文学专业的同学也纷纷跑去听课。这些演员或作家虽然不是专业老师,但听他们讲课的学生却是热情极高,大教室的阶梯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的种子就开在中文系学生心中开始萌芽了。
我记得马季讲课时说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有一次他乘公共汽车,车到站后乘客先下后上,排队的乘客都上了车,汽车即将关门,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从不远处急急忙忙跑过来,边跑边喊“等一等!”司机好心等着他,中年男子赶到车门口,猛地窜上了车,由于速度快,惯性大,没能收住脚,不小心地碰了一下前面的年轻女孩。女孩子扭头冲着中年男子撇了一下嘴,讽刺了一句:“德行!”中年男子可能是书读得太多了,歉意地纠正说:“对不起,不是‘德行’,是‘惯性’……”惹得车上很多人都笑了。马季说的这个故事后来编进了他的相声作品里。马季要没有这次乘车实践,就不会有这个相声包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到河北三河市采访,得知著名作家浩然先生就住在这里,便专程到他家去拜访。我与他说起长篇小说《艳阳天》在当年的家喻户晓,荣辱不惊的他只是淡淡地笑着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我一直生活在农村……”我又说起当年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的事情,他居然还记得,笑笑说:“那都是上面安排的,我那时讲课也是勉为其难啊……”


上面照片中是我们班女同学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们班部分师生留影


北大中文系百年时我们班部分同学在曾经住过的32楼前留影


北大120年校庆时部分同学留影




北大120年校庆时我们班部分同学在未名湖畔留影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