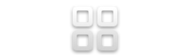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国务院发布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主要聚焦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等问题,并谈了现代化都市圈培育问题。现代化都市圈的同城化程度要达到更高的水平,除了交通物流方面的基础设施硬件互联互通以外,也需要解决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等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问题是:政府政策工具箱里有哪些工具可以使用?历史上有哪些启示推动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未来我们怎么样做得更好?现代化都市圈的同城化为何难以推进?比如我们所在的京津冀都市圈,上海所在的长三角都市圈,以及成渝、长株潭、西咸等地区,在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群建设中,中心城市与周边市县如何协调发展是大家讨论的核心问题。
城市的规模不同,但是各有各的苦:超大特大城市的苦是难以为继的“大城市病”,需要疏解产业和人口。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苦是遭受虹吸效应,“灯下黑”“吃不饱”。每个个体城市都呈现原子化发展,中心城市“吃肉”,而周边地区“喝汤”“啃骨头”。行政辖区交界的地方原本应该是最有生机活力的地方,但是却发展得不好;各个城市“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观,带来的零和博弈、负和博弈都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企业数量都是存量的情况下,就出现“挖墙脚”的招商引资;在人口出生率给定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抢人大战”,这里人多,那里就必然人少。
这些都是现代化都市圈在同城化发展时面临的问题。那么,如何打造都市圈共同体,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我们在交通物流等硬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疏解转移、市场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我最近做了历史档案研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上海刚刚解放时,1950年上海人口普查有502万人,1954年就达到699万人,两三年时间人口上涨了约50%。当时政府认为人口流动大部分是带着盲目性的,因为上海生活好“混”,供应标准又高于其他地方,大大吸引了一部分外地人口流入。所以,上海市人口办公室在1954年发布了《关于上海市紧缩人口的规划、指示、计划》,要“积极地有计划地紧缩人口”。采取的措施包括动员江苏、安徽、江西的外来农民回乡生产,在周边省份移民垦荒,推广节制生育,管理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等等。
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些政策是非常徒劳无益的。如今上海人口已经达到了3000万,人口生育率却是0.6%,基本和韩国一个水平。上海当时就是都市圈的中心,到现在还是。对于现代化的都市圈来讲,这样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
同城化的核心要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价值本位
基于此,我们从国家层面所理解的同城化和实际实现的层面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在谈同城化时要求“以省为代表统筹”,但都市圈都是跨省的;少数没有跨省的也面临省级没有办法协调的问题,比如副省级城市的问题。
因此,第一要建立更高规格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跨地区乃至跨省份的统筹协调。让中心城市作为“老大哥”来“分饼”“切蛋糕”,结果就是现在这样的“一核”独大。所以,要提高统筹层级,在更高层面上统筹,避免城市相互“挖墙脚”“以邻为壑”。
第二要重构都市圈内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的“指挥棒”,扭转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在考核评估方面,考评的单位也要放大,不能一个城市、一个县地考核。我们调研发现,现在所谓“功能区规划”,虽然有规划,但最后考核时,还是看那几个关键指标,如GDP、财政收入、人口等,而不是看你对周边城市有什么贡献,和周边城市有没有形成紧实的合作。
也就是说,我们想促进同城化,但做的动作是反着来的。所以,非常关键的是要关注这些地方官员的“指挥棒”在哪里,激励结构在哪里。要从这个痛点出发,去推动城市化发展和都市圈推进。
第三,创新产业协作、利益共享、指标转移等激励机制,便利人才、企业跨区域流动。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这个政策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意味着之前发达地区招商引资的时候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但现在欠发达地区不可以“抄作业”了。
类似这样的问题,在人口、企业跨区域流动中非常明显。比如,我调研一些企业发现,所有搬迁政策都规定是可行的,但企业发现真正搬的时候却搬不走。最后企业只能妥协,把壳留在这里,企业搬走,这样相关的财政税收指标可以跨地区共享。人才流动也同样如此。比如,某省经常强调人才的“柔性引进”,就是人为我所用,但人我不要,因为人也不会来。所以,我们在推进同城化时,还有很多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总结来看,同城化的核心是打破行政区隔,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价值本位。但是,讨论这个问题时,要特别关注同城化、都市圈的发展背后的激励机制,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创新来做对激励,让自利的城市可以利他和合作。
我们要有城市的“问题化”思维,一些深层次、难以短期改变的问题,值得我们更多地关注。城市化要更加体现政策的价值,要对更多基本问题有方向性的判断,并基于此提出解决方案。
最后,讨论城市时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国家的视角,一个是人民的视角。政府关注的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整齐划一的计划秩序,而自然秩序应有的样子却并不重要,甚至成为政府加以规训的对象。我们更多要看的还是人民是怎么思考的。当人民的视角和国家的视角出现冲突时,我们如何调和、理解它,让城市秩序不是简单化的,而是归于自然的,才能达到我们期待的效果。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