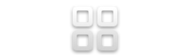他的博物馆设计,将风格视为融汇和智慧,但同时也视为束缚,他从来不会屈服或承认自己作品的单一性,1998年曾获得普利策奖的他,被评审团誉为媲美“文艺复兴古典三杰”,李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布鲁内莱斯基,能够受到这样的赞誉,当今建筑界唯其一人耳。他就是建筑师伦佐·皮亚诺。他的作品回顾展现正在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展出,截止到2019年1月20日,他对建造建筑的爱,体现在整个展览中。

展览现场
拥有场地精神的鲁滨逊
皮亚诺曾经将自己比喻成《鲁滨逊漂流记》里面那个注重气候、氛围和场地精神的鲁滨逊。在丹尼尔·笛福的小说中,鲁滨逊孤身一人在孤岛上种植植物,驯养山羊,制作陶器,离开小岛后还将小岛打造成一座新的“城市”。这种场地精神和开创精神在皮亚诺身上也有。皮亚诺的场地精神体现在对当地的考察,建筑的融合,他对设计项目具体位置附近建成多年的知名建筑的搭配,使得他的建筑和已经建成的建筑相得益彰,熠熠生辉。例如勒·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旁的建筑,哈佛大学的卡彭特中心(Carpenter Center)旁的建筑,以及在路易·康的金博艺术博物馆(Kimbell Art Museum)旁的建筑。皮亚诺还有着鲁滨逊一般的顽强,如同蓬皮杜去世后,毁约的法国建材公司,令建筑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进程一度搁置,皮亚诺则从德国连夜偷运材料,最终1977年建成了这座艺术中心。
皮亚诺的设计开创性十足,设计于1987年对外开放的梅尼尔收藏馆,他设计了吊挂于钢结构上、呈曲面状的预制混凝土反光板。此如机翼般优雅曲面造型的反光板,是皮亚诺与结构大师彼得·莱斯(Peter Rice)合作的创新发明,不但将自然的光源神奇地漫射于展示厅内,更彰显了清晰的结构与科技的结合。这种开创精神是对文明的反思和对禁锢的冲破。鲁滨逊就是一个顽强和创造的符号,仿佛无论何时提及鲁滨逊,我们依然认为他在继续着冒险,并且永远有能力生存下去,此之于皮亚诺在建筑界,也是如此。

让-马里·吉巴乌文化中心在努美阿(1998年)
1969年是皮亚诺人生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32岁,设计了日本大阪的工业亭,这座建筑受到了后来皮亚诺的好朋友、同事、竞争对手,同样也是优秀的建筑设计师罗杰斯的赞赏。二人因此结识,成就了后来若干闻名遐迩的皮亚诺的建筑作品。皮亚诺曾说“热爱传统并不等于复制传统”“ 要谨慎我们会被那些叹为观止的遗产麻痹迷惑”,作为“高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挑战自然和人力的精神。对历史的冷眼旁观,不代表对文明冷漠,皮亚诺所做的既不是炫技,也不是对文化基础视而不见。1971年,皮亚诺与罗杰斯合作,参加了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国际竞赛。在680多个竞赛方案中,荣获了竞标,设计中的电梯、管道、结构等等的外露,以及对于空间的分割,宽阔的广场设置,对于一个艺术中心来说,在当时确实是令人震惊的。这种外露的方式和巴黎的铸铁装饰传统非常契合,但是这座建筑花了30年令众人接受,同时越发地在审美上感到臣服,这座建筑的体验之独特,令蓬皮杜艺术中心在互联网占据了人类一天大部分时间观看体验的今天也能够越来越多地吸引全球热爱艺术的爱好者。当下恐怖主义的阴影、私人机构竞争以及博物馆开支的增加,令欧洲的博物馆近几年来的参观人数都遭受了重创,并不以海外游客为主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数量却未减少,反而增加了不少,这与该建筑的设计调性和吸引的人群不无关系。

展览现场
让·马悉·栖包屋文化中心(Jean-Marie Tjibaou Cutural Center,Nouméa -New Caledonia)是皮亚诺设计的一座又原始又浪漫的建筑,这座建筑作为皮亚诺设计的另一个端点,与蓬皮杜的科技、硬朗形成两极。该建筑用了8年时间完工,在这期间,皮亚诺不断与这座南太平洋神秘岛屿提那(Tina)半岛上的原住民、人类学家、生态学家、当地官员等进行商讨,最终呈现出了艺术与技术合唱的优美建筑。这座建筑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大建计划书”中的收官之作,为了纪念当地原住民和平主义者让·马悉·栖包屋所做,也同时作为卡纳克文化推动委员会的总部,保存和活化卡纳克文化。在这座建筑的设计中,皮亚诺坚持没有落入“形式象征”或者“风土符号”的窠臼,该建筑的弧形栅栏式外立面,与矗立的松林、榕树形成优美的对比,他理解当地人将房屋视为生命与环境的一部分,房屋与肉身同生同灭,可以归化于茫茫自然土地中。在皮亚诺的设计日志中,记载了他对于这座建筑惊人灵感闪现的刹那,他领悟到在卡纳克人的观念中建筑过程与成品一样重要,于是他将这座建筑设计成不断编制的形态,也暗喻生态的永续发展的展望。这座性感的建筑如同高更的塔希提少女,充满了野性、淳朴、原始感与背景的厚重。

惠特尼美术馆
建筑的重要时刻,激情、灵敏和自由
对事物的灵敏度和广泛性,令他没有墨守成规般地遵循家族的传统成为一个建造商,用一次次设计打破了建筑师作为受雇者的订单执行人属性,让建筑本身成为拥有语言纬度的平面和立体的现代交响舞曲。一位建筑师首先也应该是一位工程师,柯布西耶曾在他的《走向新建筑》中写道。然而建筑师的理性、计算、规划以及对委托人、预算的妥协,往往让建筑师逐渐失去激情,失去一种感性的存在。“不存在不带有情感的艺术,也不存在没有激情的情感。在采石场中沉睡的石头是没有生命的,但一旦它装饰在圣彼得大教堂的拱顶上,就成了一出戏剧。”这是柯布西耶在曾经评价米开朗琪罗的篇章中所提到的,但是由于资本的发展,市场的快速竞争,以及所谓风格正义,在现代艺术开创以来愈演愈烈,许多设计师放弃了在剖面和轮廓上对于自由的追寻,只一心寻找资本的气味和实用的功能性结构。但是剖面和轮廓作为建筑师的试金石,在皮亚诺的建筑上给了放弃激情和自由的艺术家们的烂俗借口重重一击。
此次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皮亚诺回顾展中对皮亚诺的大量作品进行呈现,让观众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他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实验性所需要的广泛的应用思维,不同技术手段、材料都能为他所用,这种自由的境界,是热那亚一贯的人文情怀在个人身上的映射,也是皮亚诺本人的理想。他曾提出过“人文城市”的模式,他的建筑手稿中,经常有对一天中不同时间的自然光量和方向的考虑,在他的手稿中甚至能看到他对光线随着距离和在建筑中传播的考虑,而这些考虑在手稿草图中,并非是通过画面效果的渲染达成的,而是作为设计的一部分的明确思路,这是非皮亚诺对自然的灵敏所不能造就的。

惠特尼美术馆
意大利的现代设计是在战后才得到世界的公认。与芬兰非常相似,意大利现代设计的民族特征独特、个人化,而皮亚诺将这种民族特征具备了国际视野,他试图通过对文化的判断和筛选,实现对不同文化之间壁垒的消解,比如从最初时期高技派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到最近的纽约惠特妮博物馆的美国艺术馆,以及位于洛杉矶的美国影艺博物馆,都在诠释着他的一个理想:让精英建筑更可接近。可见皮亚诺用自己的建筑实现着人类文化自由之理想,对于隔离和文化歧视的俯视和碾压,成就了我们对于所谓“民族精神”的全新视角。建筑在试图实现我们的不安、恐惧、舒适、孤独、对知识的荣耀化在空间中的体验,我们对于人类生存方式的自由追求又能达到何种极致?他曾说道:“让人们继续活着的不是曾经做过什么,或者成为过谁,而是未来会成为的和将要做的事”。作为一个“革命家”,皮亚诺就是这样,迅猛地发现、推翻和改变着建筑空间的规律,以及人造物与自然的秩序。(文 Article > 张云平;图 Pictures > 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