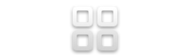沙市码头之二——江边的码头
张 俊
清末时,沙市就有“小汉口”之称。世人之所以如此赞誉,其中一个原因是沙市同汉口一样,在江边建有多座码头。沿江一带桅杆如林,轮船进出,客货流动,机声不息,显示出一座开埠商城的兴盛活力。

民国初期“洋码头”的大趸船
其实,这样的情形早在清中期即已形成,“贾客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船,向晚蓬灯远映,照耀常若白昼”(清《荆州府志》)。沙市南有长江,北有长湖,中有沟通长江与汉江的“两沙运河”(沙市至沙洋),天然优越的水运条件为沙市商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那时的沙市江边,万城大堤(今荆江大堤)外边还是泥沙地,没有固定的码头,木船到了沙市,行船者见缝插针地择地停泊。江边有固定码头,那还是清同治年间的事。同治十二年(1873年),荆州观察史孙家榖令江陵县令兴修驳岸,驳岸既可固堤,又便于木船上下客货,于是江陵县令找沙市“十三商帮”出资修建。待驳岸修好后,船民们纷纷“立旗划界”,抢占地盘,建立供本帮木船停靠的码头。一时形成“水龙上下,巷陌码头殆五十余座”(清《沙市志略》)的布局。
到清末,一些小码头逐渐被淘汰,形成了上起筲箕洼(万寿宝塔上游),下至柳林洲的码头“长龙”,时称“三关六码头”。所谓“三关”,是指官府设在大湾、宝塔、巡司巷的三座税关。在三关地建有渡运码头,即上渡口丁公码头,渡运线为康家桥至窑金州;中渡口合众码头,渡运线为巡司巷至埠河下码头;下渡口为接官厅码头,渡运线为竹架子至埠河下码头。
所谓“六码头”,是指拖船埠、康家桥、七里庙、谷码头、竹架子和白河套处六座货运码头。当时的货物装卸一般是按同宗归类,于是便有了装卸染料的“靛码头”、装卸谷米的“谷码头”、装卸日用瓷器的“瓷器码头”、装卸生活陶器的“土陶器码头”、装卸烧炭的“炭码头”和装卸水果的“水果码头”。
沙市最古老的码头应当是“拖船埠码头”。明清时期,从长江来的运货木船若要经“两沙运河”入汉江,就得靠人力用绞索、滾木将木船拖过万城大堤。反之,从汉江经“两沙运河”入长江也是釆用此种办法。久而久之,拖船的地方被称作“拖船埠”。之后因为“两沙运河”北端的汉江倒堤,导致运河淤塞等原故,“拖船埠”便不再拖船,拖船通道也就变成了新建街,但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拖船埠码头一直到民国时仍在使用。
清末民初,沙市最大的码头应是“洋码头”。这个地方早先有两家竹行,从江西、湖南运来的竹排在这里“起坡”(指运上岸)凉晒,因而最早叫“竹架子”码头。后来官府买下这座码头,改建成迎送南北往来官员及邮差的渡运码头,因此就改称“接官厅”码头。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官府将接官厅码头交给沙市海关,由其改建成沙市海关码头。由于外轮停泊在这里报关缴税,当地人又叫外轮为“洋船”,因而停靠“洋船”的码头自然就称作“洋码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沙市码头发生“焚毁局关洋房案”,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之父)给朝廷的案情奏报称:“湖南人杨兴全由山货行挑行李赴洋码头”(《奏為湖北沙市地方焚燬局關洋房一案》),可见官府早就在这么叫。清宣统年间,官府曾将“洋码头”改名“新码头”(清《江陵乡土志》),但是当地人叫顺了口,根本就不理会这个更名,所以这里一直称作“洋码头”。
进入民国后,“洋码头”不单是指沙市海关码头,而是泛指交通右路至玉和坪的一条沿江地带。英国太古与怡和轮船公司、日本日清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的趸船都设在这里;沙市海关、荆沙关监督公署、轮船招商局沙市办事处、中国航空公司沙市办事处、美孚石油公司沙市办事处、安利英洋行、沙市天主教堂、沙市打包厂用房也都是建在这里。这里的机构、工厂、商铺等,在使用的票具、信封上都印有“洋码头”字样。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沙市海关建成水泥岸壁式码头。码头长约400多米,有3座大栈桥和2座小栈桥,以方便客货的上下。码头总造价为八千两“关平银”,这次是由清荆宜道行台拿出的银子。
清末民初,随着沙市商贸与航运的发展,在沙市设分支机构的中外大轮船公司都感到码头不够用,于是纷纷自建码头。轮船招商局沙市办事处、三北轮埠公司、日本日清轮船公司、英国太古与怡和轮船公司,包括沙市打包厂都先后建成专用码头。这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公司(厂),所建的码头无不风光气派,宽敞的石台阶、高大的铁趸船、飘扬的公司标旗,给沙市港平添了几分现代港口气息。
民国时,沙市有三处用工最多的场所:一是沙市打包厂,二是沙市纱厂,三是沙市码头。长年在码头当搬运工的有上千人,他们天不亮出门,条件好的吃碗“码肥油大”的早堂面,套上坎肩就去干活。在尘土飞扬、机声隆隆的码头,每日装货、卸货、扛包、抬包,一日复一日地辛苦劳作,以勉强求得一家人的温饱。若是哪天碰上个闪失,把人弄没了,就只有靠“三子”(用杠子、绳子、席子抬尸首)送终,人活得十分艰难。

湖北巡抚谭继洵给朝廷的奏报(原件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码头上的搬运工被分成了三类:一类是“长年工”,也叫“名子”,“名子”可以继承、出租、转卖。一个“名子”约值四五十块大洋,高的可达百余块;二类是“佃肩”,靠租借“名子”上工,每日所得须交部分给“名子”,有时“五五开”,有时“四六倒开”,总之辛苦一天所剩无几;三类是“拉荒”,这一类人属于短工,往往是干两天挣点钱就走人。辛亥首义后,不少失去“皇粮”的旗人常年在码头当“佃肩”“拉荒”,靠出卖力气讨口饭吃。
码头上的搬运工,多以籍贯划分成大小不一的行帮,其中汉阳、武昌帮的人最多,四川、湖南帮的人居中,河南、安荆帮(本地帮派)的人最少。行帮的帮首称“头佬”,“头佬”有大小之分。小“头佬”手下一般有二三十名搬运工人,而大“头佬”手下的搬运工则多达百余人。
“头佬”的收入通过两招:一是发“签子”。“签子”是上工凭证,搬运工只有拿到“签子”当天才有事做。“头佬”凭借掌管的“签子”捞好处;二是占“日子”。“头佬”按大小每月轮流到码头上管事,管事“头佬”所得红利须分给其他“头佬”一部分。大“头佬”都是有钱的人,他们通常早上坐黄包车来码头,中午去觉楼街的“软脚坡”(妓院集中地)吃花酒,晚上再到巡司巷的懋林春澡堂泡澡,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1947年,沙市同庆泰花粮行的格式发票
码头上的行帮都有各自的搬运地盘,甲帮的地盘乙帮不得擅自闯入,否则就用杠子说话。1931年7月一天,沙市打包厂经理金式如雇人从厂里往码头上搬运花包。这一带本是“洋码头”大“头佬”许德礼的地盘,他认为运花包是他的业务,便令人驱赶厂里的搬运工。厂里的搬运工仗着有青帮背景便顶着不走,为此双方展开一场恶斗,结果厂里的搬运工被打死两人。
沙市打包厂的老板叫刘季五,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接管了家族产业,1926年底来沙市建厂,一向与官场交往密切。刘季五一纸诉状将许德礼告到沙市地方法院,法院后判他五年徒刑。许德礼是沙市码头工会的头头,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所以法院对他也不敢得罪太深,便同时判令:打包厂的搬运工只限于厂区内搬运,向厂外转运花包仍须找许德礼的人来做。
1947年7月的一天,“洋码头”的“盐工队”将一艘待卸盐包的驳船开到拖船埠码头卸货,以就近将盐包入库。“洋码头”的人闯进了拖船埠人的地盘,那里的搬运工当然不干,双方当时便混战起来,结果“洋码头”的人寡不敌众,被打得落花流水。
“盐工队”队长许成章是许德礼的儿子,他仗着老子的势力,长期独霸码头盐包搬运业务。他见自己的人吃了亏,第二天便带着100多名搬运工,扛着杠子到拖船埠码头兴师问罪。

民国初期的沙市码头工会会员证章
拖船埠码头的“头佬”叫陈志道,他见许成章带人打上门来,当即喊来几百人迎战。这场恶斗先是在拖船埠码头打,后来又打到新建街、巡司巷和民乐街,前后共打了四天四夜,最后造成20多人重伤、1人死亡的恶果,直到沙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员干预才罢手。
许成章除了有老子撑腰外,还有沙市盐务支局局长孙德塾做后台,可是陈志道的身后也有两座靠山,一个是沙市商会会长徐鹤松,此公是民国总统黎元洪的义子,当过湖北禁烟总局经理,人称“徐老总”;另一个是江陵县总工会理事章兰亭,此人在抗战期间加入过国民党军统,曾任财政部湖北区货运处采购专员。抗战胜利后,这两人脱离政界回沙市做粮食生意,与陈志道是生意伙伴。徐、章二人早就不满许氏父子吃“独食”,于是暗中鼓动陈志道开打,给“洋码头”的人一点颜色看看。

1947年,沙市警察局在洋码头发布的布告
这一场恶斗,“洋码头”的人又吃了大亏。许成章便想用当年刘季五对付他老子的办法,准备将陈志道告到法院去。可还没等他递状子,徐老总就让人捎来狠话,要他就此罢休,否则便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许成章知道徐老总的厉害,也只好咽下了这口恶气。
民国时,沙市先后建有43个码头,其中“水码头”18个(沿江码头12个、内河码头6个),“旱码头”(陆地装卸点)25个。码头上的行帮为守住自己的地盘,每年打斗几次是经常的事。这样的闹剧,直到1949年之后才逐渐消停下来。
(选自《荆州古城往事1976――1949》)
打赏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