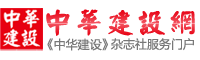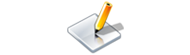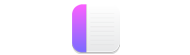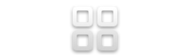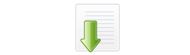荆沙水灾谁之过
张 俊
1935年7月的大洪水退后,荆沙水灾救济委员会作了一个调查:江陵县划分为六个区,各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水灾,其中以草市和沙市两区最为严重;全县四十多万人,有灾民二十多万,其中受赈灾民十二点八万(民国《荆沙水灾写真》)。
后来,武汉大学的学生又来江陵县作灾情考察,在其编写的《湖北江河流域灾情调查报告书》中称:江陵(辖沙市)受灾面积二千八百二十一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7%,其中淹田一百六十多万亩、毁屋九千七百零七栋、死畜七千五百八十四头;灾民五十一万多人、淹毙三百七十九人(《沙市水利堤防志》)。

1935年7月,荆江大堤得胜台堤段溃口情景
这次大洪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在发生之初,即有人在议论,这场灾难是由人祸而非天灾引起的。在洪水退去之后,社会各界很快将议论的焦点集中在是人祸还是天灾问题上。如果是天灾,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但如果是人祸,则应该有人站出来领罪,并以死来谢罪。就在人们为这事议论纷纷时,荆江堤工局和江陵县政府的人,为谁该负主要责任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双方的争吵有两个焦点:第一个,究竟是谁负责管辖的堤段先溃口。荆州城西北处的阴湘城堤又称北堤,是防止沮漳河泛滥的子堤,由江陵县政府征收“北土费”,并负责子堤的防护。荆州城南边的荆江大堤又叫南堤,是防止长江大水的主堤,由荆江堤工局征收“南土费”,并负责荆堤的防护。江陵县政府的人说,这次大水是因为荆江大堤的万城堤段先溃口,倒灌的江水又冲垮了阴湘城堤,才造成了这场灾难,因此,主要的责任在荆江堤工局。而荆江堤工局的人的说法与此相反,称有可靠证据可以证明,是阴湘城堤先溃漫,泛流的沮漳河水浸坏了万城堤段的堤基,这才造成了荆江大堤的溃口,这主要责任当然在江陵县政府;
第二个,荆江堤工局局长徐国瑞和江陵县县长雷啸岑,两人中谁该负玩忽职守之责。指责徐国瑞的人说,徐国瑞平时只注重沙市堤段,长期忽视万城堤段的修防,而且该堤段在溃口之前,前去排查险情的荆江堤工局主任吴锦棠见势不妙,在留下几个人敷衍抢险后,自己逃之夭夭了。大洪水发生后,徐国瑞不紧急组织抢险,只晓得在江边祭江神,装神弄鬼,无所作为,他显然没有恪尽职守。而怪罪雷啸岑的人则说,大洪水围城时,雷啸岑居然问属下:阴湘城堤是不是在当阳,作为地方父母官,防洪是第一要务,他居然连境内的堤防在哪里都不知道,可见他是一个何等的“糊涂官”。此外,当众人都在拼死抢险时,雷啸岑却带着卫兵跑到东门教堂里躲水,贪生怕死,擅离职守,这样的“糊涂官”该枪毙一百回。

1935年7月,洪水退后,掩埋尸体情景
徐国瑞作为荆江堤工局长,这次荆江大堤出了大事,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他当然都负有不可推御之责。而雷啸岑作为县长,阴湘城堤发生了溃漫,当然也是难辞其咎。他俩都深知这次灾祸巨大,随之而来的处分将会很重,所以都挖空心思找理由,要将责任推给对方,以为自己摆脱干系。
雷啸岑是湖南嘉禾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年四十五岁。他是国民党政学系的干将,1931年经政学系头头张群、杨永泰等人的推荐,到荆沙任湖北第七区(后改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江陵县长。他上任之后,在肃清地方匪患、整饬官场风气、改良中小学教育等方面做了一些实事,一度有人叫他为“雷青天”。
雷啸岑是个有心在仕途上求发展的人,因而对于不利于他的非议,首先主动地进行了回击。1935年8月,他在上海《时事新闻》上发表《江陵洪水围城记》一文,详叙了洪水围城的经过,同时强调了两点:一是这次洪灾是因为荆江大堤的溃口造成,徐国瑞局长应对此负全责;二是他带领县府的人竭力抗洪,已尽到一县之长的责任。
雷啸岑的文章就像一枚炸弹在荆沙上空炸开,引起荆江堤工局、沙市商会和驻军长官的强烈不满。徐国瑞,字兰田,湖北应山县人。他早年参加过武昌首义,民国后曾任荆州水警区长、荆宜水警厅厅长兼两湖巡阅使署参议、长江上游总司令部顾问,授少将军衔。徐国瑞与原荆江堤工局局长徐国彬交情较深,1923年徐国彬去职时,力荐徐国瑞接替了他的职务。

湖北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江陵县县长雷啸岑
徐国瑞在出任荆江堤工局局长后,平时很注意与当地各界人士搞好关系,特别是与几任驻军长官,如张发奎、刘和鼎、严敬、郭勋祺、徐源泉等人都保持着较好的交往,尤其是与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的交情不浅。徐源泉在推行“新沙市建设计划”时,聘他出任市政整理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他为地方建设事宜也的确是尽力奔走,因而他为人做事的口碑一向不错。雷啸岑撰文将矛头直指徐国瑞,沙市商会的何瑞麟会长等人不敢说话,怕得罪县太爷,但是徐源泉却指示部下为徐国瑞抱打不平。
不久,徐源泉的秘书皮震在《武汉日报》上发表了《驳江陵洪水围城记》,他用大量事实证明,雷啸岑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他也用肯定的语气声称两点:一是因为阴湘城堤溃漫,才引起了万城堤段溃口,主要责任在雷啸岑;二是雷啸岑贪生怕死,自己带着亲信逃入东门天主教堂偷安不说,还用船将家眷偷偷地送往沙市避难。
徐国瑞在争吵之初没说什么话,他除了去组织堤工堵塞大堤溃口之外,就是到章华寺去为死难者做法事超生。徐国瑞虽说是行伍出身,但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是沙市居士林的居士,还是章华寺的大护法。1923年,高僧太虚法师到章华寺讲经,就是他亲自带一条小轮船,从松滋县的江口镇接来的。他深信荆江大堤若是在汛期安然无恙,那一定是得益于佛祖的保佑,因而在每年的长江汛期过后,他都要在中秋节那天摆酒请客,欢庆安澜、礼谢佛祖。

荆江堤工局局长徐国瑞
1935年7月6日那天上午,徐国瑞去万城、马山一带察看水情后,就知道大事不好,于是在下午让人准备了“三牲”,偕同沙市商会会长何瑞麟等人,在沙市大湾处的堤街上设了香案祭祀江神,并将一筐筐的食物抛入江中,“以飨江蛟”, 祈求洪水速退(《荆江堤防志》)。第二天,徐国瑞又让人在荆江堤工局门前设香案,又搞了一次祭祀江神仪式。他还以荆江堤工局的名义致函沙市公安局,提请该局向市民发了个“禁屠三日,冀感天和”的布告(民国《荆沙水灾写真》)。
在徐国瑞看来,他这么做,不过是效仿古人而已。据《梁书》记载,天监六年(507年),荆州大水,江溢堤坏,始兴王憺亲率将吏冒雨筑堤。雨大水猛,憺杀白马祭江神,倒酒于江流,结果是水退堤立。既然“祭祀江神”是古人行之有效的大法,他徐国瑞当然要拿来一试。徐国瑞声称,他在做这些事时,并没有忽视履职,而雷啸岑指责他,是想将自己之责推在别人的头上,这使徐国瑞很是愤怒。
徐国瑞早就知道,雷啸岑在发表那篇文章之前,就将荆江水灾的情况向湖北省政府写了报告,说水灾是因万城堤段溃口造成的,省政府主席张群信以为真,便让江汉工程局向荆江堤工局发来训电,除了对徐国瑞严责外,还令他抓紧抢筑溃口,否则严惩不贷。徐国瑞感得雷啸岑欺人太甚,于是也向上峰写了一份《荆江堤工局报告书》,并拿到《荆报》上发表,以为自己作辩护。
徐国瑞对江陵县境内的山川河湖了若指掌,因而他在报告书中驳斥荆江大堤“先溃论”时称:“阴湘城内堤(方官堤)在横店子(属万城堤段)上五六里,外堤(吴家大堤)又在上七八里,其地势与横店子堤顶实高七八尺。如云阴湘城堤系横店子(在万城堤段)溃口流冲,则是水不就下而反攻上,断无是理!况横店子漫口系在七月六日早,阴湘城堤溃口系在七月四日下午,相距一日夜,岂有先溃口之水,不淹城(荆州城)草(草市),后来之水而淹城草乎?”
他在报告中还用讥讽的口气写道:“瑞非敢与雷专座辩论者,如谨奉雷专座任何严令,只有隐忍承受,不辩一辞”(民国《荆沙水灾写真》)。
在徐国瑞的那份报告书发表之后,驻军司令部政训处的韩浚等人对不利于徐国瑞的言论采取了一些打压措施;特别是在这年七月,沙市商会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发去一封《请奖抢险出力人员电》,恳请对四个抢险有功人员给予特别优奖,这四人中就包括徐国瑞。如此一来,舆论便渐渐地倒向有利于徐国瑞的这一边。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面对如此局面,雷啸岑也是无多话可说了。
这次大洪灾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不处理官员难以平民愤。为此,国民政府和湖北省政府最后还是对雷啸岑和徐国瑞都做出了处罚,徐国瑞受到的处罚是“降二级改叙”,留任荆江堤工局局长一职,他在任上又干了好些年才退下来。1946年徐国瑞因病去世,其遗体在章华寺火化,时年六十五岁。
1936年,国民政府对雷啸岑也做出了处罚。这一年,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刘侯武、白瑞、杜忱三人,向监察院于右任院长提交了《提劾湖北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江陵县长雷啸岑横暴贪污疏忽救灾案》,除指控他鲸吞田亩捐、伪造薪饷报销、滥用逮捕职权等罪名外,还指控他在1935年水灾时犯有两项罪名:
一是疏忽防汛。“此次阴湘城堤溃决,该专员事前并未亲往该堤查勘,乃至该堤漫溃时,尚不明其真相,并不知阴湘城外堤之别名为吴家大堤”(民国《提劾湖北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江陵县长雷啸岑横暴贪污疏忽救灾案》);二是抢险不力。“江陵洪水围城时各界代表开会,成立临时水灾预防办事处,讨论临时应付紧急抢险办法,并订逐会商一次。该专员为地方行政长官,责任何等重大,乃自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二逐日会议,计举行六次,该专员竟未出席一次。当七八日水势最猛之时,该专员避居东城天主堂,并饬人在公安门城上及鼓楼上搭席棚,以备不得已时为专员、职员之避所。其为自身安全而不顾大局,实属渎职”(引文同上)。
后来,国民政府监察院通过了对雷啸岑的弹劾案,雷啸岑被撤销一切行政职务。之后经张群的推荐,被撤职的雷啸岑去四川任过重庆市教育局局长、《华西日报》社社长兼总主笔等职。1947年,张群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雷啸岑在行政院也谋到了一个职位。1949年7月,雷啸岑去了香港,曾任《香港时报》总主笔。1982年他在香港病逝,享年八十六岁。
其实,在雷啸岑走后,还是有不少荆沙人时常念起他的好,因为他在江陵县县长任上,十分注重发展荆沙的地方教育。当年就是他下令,要利用沙市商帮的会馆办小学堂,这才使一大批穷苦孩子有机会上学,并从此改变了人生命运。
(选自《荆州古城往事1876――1949》
打赏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