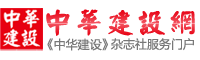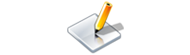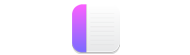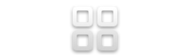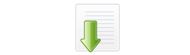荆沙水灾大救援
张 俊
沙市商会的办公地在聚兴诚银行楼的西侧,大门朝着中山马路,进门后有一条长廊,走到尽头是一间会议厅。1935年7月9日下午一点,荆沙各界的一百五十多名代表在这里聚会,会上决定成立荆沙水灾救济委员会(简称“荆救会”),以组织社会各界对灾民进行救援。

“荆救会”主任杨绍东
沙市商会会长何瑞麟德高望重,按理说应由他来主持今天的会议,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再说抗洪救灾要依靠驻军,所以众人便推荐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的杨绍东参谋长来主持会议。杨绍东四十来岁,身材瘦高,为人处事精明干练,是徐源泉军长的得力助手。前天下午,杨绍东就召集沙市城区的联保主任开会,就成立“荆救会”的事商议过一次,因而九号的这天会议,很快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推荐徐源泉为该会主席;二是成立“荆救会”章程起草委员会,杨绍东责成驻军司令部秘书彭凤昭先拿个草案。
彭凤昭是黄陂人,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复兴社的一员干将。他原来在一所学校当教书先生,后受复兴社湖北省干事会的委派到徐源泉的司令部当秘书。他脑子灵活,文笔又好,平时除了起草军令外,还常以徐源泉的名义在《新沙日报》发表文章,因而很受徐源泉的赏识。
彭凤昭是文章快手,他第二天就拿出了章程草案。按这个章程,“荆救会”下分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执行委员会,由杨绍东任主任,该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筹赈”“放赈”“监赈”三个股,负责办理救灾具体事务;另一个是监察委员会,由沙市商会会长何瑞麟、副会长汪润之负责,主要监督赈灾钱物的发放。

“荆救会”监察委员会主任何瑞麟
七月六日早晨洪水袭来时,沙市郊外不少人来不及跑到高处,情急中只好爬上了屋顶,或者是树上,经过几昼夜的苦熬,绝大部分人已经奄奄一息,将他们救出来刻不容缓。所以,“荆救会”组织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船去沙市郊外救援。其实救援行动从八号那天就开始了,按照杨绍东的命令,能找到的船都被集中起来,在装上馒头、锅块等食物后,即由放赈人员押船去郊外水域搜救幸存者,随时予以施救。
派往沙市近郊的船很快就救回了一百六十多人,但前往荆州城的二十多只船却没有那么顺利,船队好不容易行到荆州城墙附近,却发现这里风大水急,救援异常艰难,“舟抵五眼桥(荆州城东门外),水流甚急,呼救之声,不绝于耳。马河(今护城河)中流,波涛汹涌,见灾民十余人,或身坐木盆,或手挟木板,有尚未落水者,有半身入水者,回流冲激,左翻右荡,时东时西,忽起忽伏,口呼救命,距记者所乘船约十丈。同人不忍,均以木板代桨,极力推进,奈水流湍急,浪涌入舱。同人不顾危险,仍奋勇以赴,数进数退,均未越过。浪中灾民,亦相去渐远。本船方拟再进,忽狂风大作,险遭覆没。再观呼救之人,已卷没波心,呼声于怒涛澎湃中已不甚了了”(民国《荆沙水灾写真》)。

1935年8月,“荆救会”搭建的灾民收容所棚屋。左一为棚屋设计者王信伯工程师
尽管搜救行动十分危险,但押船的放赈委员仍令船工尽力救援,沙市商会、沙市感应堂和沙市圣公会等组织也雇船参与了营救行动。从八日至十日,几十只木船昼夜不停地在荆州城与沙市之间的水域实施搜救,这才使不少人捡回了一条命。
这次荆沙的水灾空前惨烈,靠地方自救已不能解燃眉之急。为了尽快救济灾民,荆沙当局、各民间社团都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各种渠道向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驻鄂绥靖公署,仍至全国大社团反映灾情,呼吁尽快对荆沙实施大救援。
荆沙遭洪水侵袭时,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在恩施忙于军务,他得知水灾消息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荆沙是他的防区,驻军的后勤基地又设在沙市,一旦泡汤,自己的那点本钱就全完了。因此自从水灾发生之后,他一边令杨绍东全力配合地方抗洪,一边三天两头地向上峰发电求救。徐源泉是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二级上将,平时出言谨慎,但这次为了能引起高层的关注,他将一些捕风捉影的事也写进了电文:“荆州城四面皆水,居民数万,平时粮食均仰给于沙市,刻为水阻,无法购运;倘不急救济,则不死于水者,将悉死于饥。并见有饥饿不堪之老妇,将其所生之子,剖而食之,尚有两腿,置诸怀中。此情此景,想较古人易子而食,杀妻饷兵,尤为痛心。”(民国《荆沙水灾写真》)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一些民间社团也纷纷向外界大声疾呼救援。七月十日,“荆救会”向全国发出一封求助通电:“天灾荆沙,洪水泛滥,数十万生灵涂炭,半葬鱼腹,半作哀鸿。十余县田庐禾黍,或成泽国,或付东流,惨目伤心,实为近百年来未有之奇灾。特电恳乞,迅颁急赈或派员来沙直接散赈”(民国《沙市市政汇刊》)。本地的《荆报》为了配合求援呼救,还专门请沙市显容照相馆的人去拍了大量的水灾照片,并通过《大公报》等报刊登出,以期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七月十一日,“荆救会”又派荆沙海关监督许风藻专程赴南京,去向财政部长孔祥熙面呈灾情,恳请国民政府尽快拨款拨物救援。荆沙之地发出的强烈呼吁,终于引起国民政府高层的重视。

沙市商会代表贺吉甫在街头为灾民募捐
1935年7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乘一架飞机飞临荆沙视察灾情,“行营主任张学良氏,乘巨型机由汉来此视察。午后四时,即闻机轧轧,破空而来,在本市顶上盘旋一周,继飞草市一带,旋即渡江而南,视察公安及属虎渡一带后,复回绕本市多时,始循原线飞汉口。”(民国《荆沙水灾写真》)张学良返汉后即向蒋介石委员长报告了荆沙水灾惨况,之后又将荆江大堤溃口的情况向湖北省政府、荆沙当局作了通告。七月二十七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向“荆救会”发来专电:“已令湖北省政府统筹救灾矣。”(民国《荆沙水灾写真》)。
在千呼万唤之后,湖北省政府终于拨给荆沙五千块大洋,之后湖北省水灾视察团来荆沙时又送来三千块大洋。官方的这点钱显然是杯水车薪,看来救援还得靠当地人自己想办法。“荆救会”的人为筹赈灾款简直想破了脑壳,他们先是在报上登出《捐启文》,而后又派人向本地富商送去捐册,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要每人至少捐两百块大洋。为了从民间多筹点款,他们又弄来一些电影胶片在中山公园的中山纪念堂放映。与官方的吝啬相比,民间人士的援助则慷慨多了,“荆救会”前前后后收到社会捐款多达三万多块大洋,此外还收到面饼五万多斤、药品八千多包,这些雪中送炭的援助帮助许多灾民渡过了难关。
从沙市郊外逃到城区的灾民大多都是两手空空,进城区后既缺吃少喝,又只能露宿街头,一些人病了也无钱医治。为了临时安置好这些灾民,“荆救会”在赶马台和章华寺建立了两个灾民集合处,所有灾民都由各辖区的警士带到集合处登记,领取《灾民证》后,凭证去文星楼贫民工厂、江陵县立二小和马王庙灾民收容所食宿。在收容所内派有管理员,实行“十户一甲”排号管理。难民们在这里每天可喝到两碗稀粥,虽说是不够塞牙缝的,但好歹可以果腹充饥。这几处收容所前前后后收容的灾民,一度多达六七千人。

1935年,参加救援赈灾的《荆报》采编人员留影
七月九日大水开始消退之后,疾病又开始传染开来。先是收容所中的老幼弱者病倒,随后一些青壮年人也倒床不起。发病轻的上吐下泄,重的则奄奄一息。“荆救会”有个卫生股,他们除了组织医护人员对患者紧急救治外,还呼吁沙市医界人士参与施救。最先响应的是义成昌药号,这家药店连夜赶制了两千包“万应散”发给患者救急;随后沙市国医公会又在罗燮元大夫的带领下,在沙市城区内设立了几处急诊所,并派出医师轮流应诊。与此同时,城区内的几家西医院,也在康生医院李星阶院长的带领下参加义诊。给患者用的药都由医生开联号单,先免费在恒春茂、义成昌、大顺生、杜同兴、同合春等六家药店抓取,而后再由“荆救会”按药品成本的半价统一结账。由于医疗行动组织及时,从而控制了疾病大范围的传播。
洪水淹死了不少人,但死得更多的是家养牲畜。待洪水退去后,在太阳的暴晒下,那些尸体就开始发臭,城区上空时常随风飘来阵阵的臭味。七月十四日,“荆救会”卫生股紧急组织了三支掩埋队,在沙市公安局警士的协助下,分赴郊外收殓人与牲畜的尸体。在掩埋尸体时,先是挖一米多深的坑,将尸体放入后撒上生石灰,然后再用土厚埋。
在江水回落之后,堵住荆江大堤万城堤段的溃口成为“荆救会”要处理的头等大事。恰好这时荆江堤工局弄来了一笔修堤款,于是“荆救会”从七月十四日起,从灾民中陆续征集数批青壮年人去溃口处筑堤,让他们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挣点现钱,以应付将要到来的秋荒。
“荆救会”的赈灾活动,一直持续到这年底才告结束,事后该会在向湖北省水灾救济总会提交的报告中说:“所有办事员均系纯粹义务,并未在会内开支分文。阅时六月,集款数万,以各县灾区之广,数十万灾民之众,不无杯水车薪未能普及之恨,而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绝未有侵蚀浮滥掷诸虚杜之弊。”(民国《沙市市政汇刊》)
(选自《荆州古城往事1876――1949》
打赏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