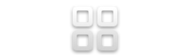草市镇被冲毁
张 俊
荆州城东门外有两个大集镇,一个是距城约十五里的沙市镇,另一个是离城约四里的草市镇。自古以来,“沙、草二市,为江陵诸市之最大者”(清《荆州州府志》)。
这两个集镇之所以兴盛,与紧临“两沙运河”有关。早在明清时期,木船从长江入汉水,或是从汉水到长江,都是走“两沙运河”。临长江的沙市镇在运河的南头,近荆州城的草市镇在运河的中段,都是转口货物的集散地。

1935年7月,决堤而出的洪水
民国时的草市规模不算小。镇上有五条纵横交错的街巷,最长的一条街为南北走向,中间一条通往运河的青石板路,将这条街一分为二,南段叫南街,北段叫北街。
早在晋代,草市就是一个漕运码头,集中在荆州城的漕粮在草市码头装船北运,送往洛阳或长安。繁忙的漕运给草市带来兴旺气象。到民国时期,草市的酒馆、茶舍、斋铺、榨房和杂货店等多达数十家,常住居民五千多人。由于草市靠近荆州城,辛亥首义后有不少满人从城里迁居这里,镇上那些扛包的、拉车的、做小生意的人,有不少是过去吃皇粮的满人。街上卖的子面锅块、血肠汤、扯糍粑、欢喜坨、浆米藕等,也多是满族人家的寻常食品。就这么一座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小镇,在1935年7月却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1935年7月6日是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一大早,天仍然像前几天那样“哗哗”下着大雨。早上六七点钟,不少人家在准备烧早饭,去运河里挑水的人突然发现,有急涨的大水漫上坡岸,不一会就逼近临河房屋的后院。很快,从北街东关桥外流来的水又涌入街心,并顺着石板路朝南街滚动。到中午时分,水淹到行人的小腿肚子,到了下午竟涨到齐腰深了。
大水刚流入街上时是清亮的,人们聚在街口议论这水的来头。有的说是沙洋那边倒了堤,从那边漫过来的;也有的说是从桥河(荆门县拾回桥)那边流过来,是太湖港的来水。起初,镇上的人都未将这事看得太严重,当南街流进了不少水,而且流水逐渐变成了土红色,人们这才想到可能是荆江大堤溃口了。有人惊慌地跑到镇公所,想打个电话问问荆江堤工局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此时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935年7月,在高地躲水的灾民
草市流传着一句戏言:“倒了南江堤(荆江大堤在草市南边),大家到长湖里去碰脑壳。”意思是荆江大堤一旦溃口,那么如同在锅底的草市镇必定会遭大水灌顶,人和物都将被冲到东北边的长湖里去。显然,此时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土红色波涛,正在应验那句戏言,镇上的人们顿时陷入惊恐之中。
草市的街巷都很狭窄,房屋大多是以“板壁房”为主,只有少数人家建有两层砖木楼房。大水袭来后,家家户户先是抢着搬东西,住楼房的往楼上搬,住平房的往屋顶搬。地势低凹的北街最先进水,一些店铺老板就忙着雇人将货物往地势高的南街上搬。这时的搬运费涨得比大水还快,搬一包川盐到南街只有几百米,但搬运工一张口就要半块大洋,高时竟涨到两块大洋。因为一包川盐要值三十多块,所以店老板口里在骂“要钱去死呀!”,最终还是咬着“牙巴骨”掏钱。第二天一早,店老板发现这搬运费都白花了,因为高涨的洪水,早已将搬到南街上的货物冲了个精光。
草市镇外的运河上有一座石拱桥,平时桥两边停满了货船和“木划子”,洪水袭来时,这些船与划子就成了镇上人逃生的希望。可是,但当人们蹚水来到船前时,发现此时想上船简直比登天还难。一些胆子小的船家怕汹涌的波浪会将船打翻,因而给多少钱都不肯让人上船,只是将船抛锚在原地不动,以求全家人自保;也有一些胆大的船工想发横财,只要有人给钱他们就开船,但是去荆州城或是沙市的船价却高得让人咋舌,平时每人两百大铜元的船资一下涨到了三五块大洋;去沙市的船,最高时竟要到每人三十块大洋。船客骂船工昧良心,只晓得赚黑心钱,而船工也不高兴,说自己拿命救人反而是背了骂名。
船上的人发现,就是人上了船,逃生的路也是一路惊险。从草市去荆州城,平时坐四五个人的木划子这时却装了一二十人。木划子在波涛中颠簸行进,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四周是茫茫一片的洪水,空中还响着炸雷,每个大浪打来都会引起一阵阵的惊呼。特别是木划子行驶到荆州城下的九眼桥时,船上人看见桥南的水面,较桥北的水面高出了一丈多,仿佛是一匹巨大的幔布在抖动时,无不吓得魂飞魄散。
乘船来到荆州城下,发现进城可不是那么容易。此时的荆州城大门紧闭,进城得靠城墙上的人往下放绳索,而后还得自己将绳子在腰间系好,再让人拉上去。倘若是绳子断了或是脱手了,人只要摔下来,瞬间就会被洪流卷走。

1935年7月,在洪水中自救的少年
真是乱世出歹人,镇码头上,还有一些船被地痞流氓控制了。他们三五人一伙强行抢了几条大船,乘人们急于逃生,未来得急收拾家中物品之机,便挨家挨户地到商铺,或者是大户人家里翻东西。这些人气势汹汹,人多势众,手里又都拿着“家伙”,没人敢对他们说半个不字。有一家糕饼店前后被洗劫了七次,那些家伙们拿了钱物不说,店老板只是嘀咕了几句,腰上就被捅了几刀,差点就送了性命。
草市北街外有一座黄家山,其实也就是个土堆子。大水来后,一家杂货店主出高价将货品搬到土堆子上,可没想到逃过了水淹却没能躲过劫匪,五袋川盐被抢走了三袋;几十石米也被抢个精光,数十条香烟更是一根不剩。劫匪们一边往船上搬东西,一边还振振有词地说:大水来了,爷们不拿也是被水冲了。与其孝敬龙王爷,不如让活人享受点。被抢的店主早就吓得半死,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自认倒霉。
草市镇上,更多的人在乘船逃生不能,又觉得上楼、上屋顶、上树都不保险的情况下,便开始扎木筏自救。这活计其实也不难,就是将竹子或木柱头用铁丝扎紧,上面再钉上门板,以作为逃生的工具。扎木筏要用铁丝,这原本是很便宜的东西,此时却卖到四两一块大洋,几百钱一圈的绳子也卖到两串大铜元。但此时急于求生的人们早已经将钱当成了废纸,只要是扎木筏所需要的东西,即便是再贵也会买来,只想快点扎成木筏逃命,因为洪水已经越涨越高了。
扎好的木筏都摆在各家门前,人们在堂屋里呆望着洪水将木筏浮起来。当屋里的水涨到齐腰深,人已经实在待不下去时,便扶老携幼地爬上木筏,然后像木桩子一样站在上面,望着洪流在木筏下涌动。这时镇上的叫卖声、织布声、榨机声等都已经消失,只有风雨声和波涛声在交相轰鸣,不时有坍塌的房屋发出一声声的闷响。
最糟糕的情况是在夜幕降临之后。当时四周是一片漆黑,波涛在耳边怒吼,大雨“哗哗”下着,木筏上不少人裹着棉袄还冷得嗑“牙巴骨”。站在木筏上的人此时又饿又累,站久了也只能稍稍蹲一下。在越来越高的洪水侵袭下,最先进水的北街房屋开始成片地倒塌,发出的轰隆声让木筏上的人听得心惊肉跳。他们担心南街的房屋也会像北街那样垮掉,如果是那样,拥挤在南街上的木筏就会失去两侧房屋的屏障,像一片片树叶般随波漂散,那样人就命悬一线了。
就在这时,木筏上的人看见沙市方向出现了稀疏的灯光,先是星星点点,而后是一片昏淡的白光,于是便有人开始咒骂,骂沙市人心如毒蝎,见死不救,只晓得醉生梦死地享受,“想到那电灯光下底葡萄酒杯,陶醉在大饭店阔少们迷恋着的醇酒和少妇,真令人恨之入骨。这近在咫尺的灾民,你们在电灯光下安住底沙市人们,都不想救济么?那时我要是能放毒瓦斯,一定要将大量的毒瓦斯放出,来毁灭沙市安逸的人们”(民国《荆沙水灾写真》)
其实,草市人是大大地误解了沙市人。在六日洪水袭来这天,沙市公安局就接到湖北第七区行政公署专员兼江陵县长雷啸岑的电话,让他们迅速派船去草市一带救人。该局奉命后,当即雇船二十余只前往,但因为风雨太大,只救回了五十余人。与此同时,沙市商会也派船前往荆州城和草市一带救援,但船行到中途时,终因水流过急而不得不返回。

1935年7月,沙市商会派船在荆州城公安门外赈灾
在六日晚上七时左右,沙市商会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成立若干个救灾分组,于次日分头再去灾区救援。派往草市的是李铁农和李舜卿两人,李铁农是当地的名记者,对荆州城和草市一带的情况熟悉。第二天一早,他带领的船队在驻军派出的十多名宪兵护送下,载着一些锅块和药品匆匆驶往草市。
这时的草市镇,房屋已经基本上都被冲毁,木筏也早已被冲散,只剩下一些人在残存的房顶或树上等待救援,呼救之声不绝于耳,其状况惨不忍睹。事后,一个随行的《荆报》记者作了这样的记述:“草市只余一沟乌痕……突见距船约二丈处,涌出一人,身伏木板,手握一盆,方出水面,复又下沉。同人急将船推进,始将其救起,放置船头,已奄奄一息。旋将其淫衣换下,因吃水不多,移时庆甦。据云:姓赵,草市西北乡人。因前日水来过猛,左右邻居,多遭灭顶。捷足者均逃赴高地,或攀登树顶,呼号待救。已因三日未食,饥火中烧。旋于水流中捞获屋料多件,因扎成木筏,欲借此逃生。同行者十七人,行至中流木筏被浪冲散。已幸手握一盆,复蒙诸公救援,方免于难。余十六人已不知去向云。言毕泪流不止”(民国《荆沙水灾写真》)。
沙市的这次救援行动虽说是稍晚了点,但还是有不少灾民被救了出来。之后又连续数天展开救援,救出的人都安全运到沙市灾民收容所安置。
七月八日这天中午,天空突然放晴,荆州城内的人也雇了船往草市一带救援。“本日水势虽未减退亦无增涨,城里人心稍安,城外哀鸿遍野,于是雇船十余只,派员押护,开往东北城外及草市一带分别救济难民来城,前后共计五百余人”(民国《荆沙水灾写真》)。在沙市和荆州城派出的船只救援下,绝大部分的草市灾民逃过了死劫,但是那座千年古镇,却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余下的残垣断壁更是一片狼藉。
在草市镇建房屋是最没有安全保障的。当洪水袭来时,它既不像荆州城里的房屋,有高大的城墙可守;也不如沙市的房屋,有大堤坡可承托,只要是遇上了大洪水,那就会被急流冲成一片废墟。但尽管如此,在洪水退去后,草市人还是在残破的祖屋基础上开始重建安身之所,这就叫故土难离吧。这次大洪水给草市镇带来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但草市人并没有因此而趴下,十多年过去后,草市镇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生气。
(选自《荆州古城往事1876――1949》)
打赏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