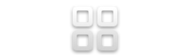刘帆笔下的荆州古城
张 俊
2013年秋天的一天,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个人,他大约七十岁左右,身材高大,浓眉大眼,嘴唇有棱角,穿着件敞开的风衣。他说他叫刘帆,是西北政法大学退休教授,童年与少年时曾在荆州古城读书,与荆州市作协主席黄大荣是同学。他今天来,是为了要本我新出的《荆州古城的背影》。我将书签名后送给了他,他笑吟吟地说:“我也送本书你,这是我退休后写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他说完握个手便告辞了,他像一阵风样地来,又一阵风样地走了。

刘帆著的《荆州纪事》
他的书名叫《荆州纪事》,当时随手翻了一下,他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其实是一本有文学色彩的回忆录,写的都是他当年在荆州古城读书和生活的往事。我那时有点忙,就顺手塞在书櫃里,这一放就是九年。前年的一个冬夜,我找资料时发现了它,便随意翻开看看,哪知一看就放不下手,竟一口气读完了。
刘帆是1941年生人,九岁那年随父母从武汉搬迁到沙洋,不久又搬到荆州古城定居。他在古城生活了八年,在这里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直到考入西安的一所大学才离开。在古城生活与求学的经历,让他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他饱含深情地在书中写道:“我真诚地热爱荆州,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我这个出生异地的外乡人,常常自称为荆州楚人,而将籍贯,我父亲的传统老家弃置一旁,那个我从未到过的地方太遥远太陌生了。我常常质疑自己:‘故乡’这个概念,在文化学的范畴内应如何界定?是注重它的血缘还是它的水土、休戚与共而滋生的情感?”
看完刘帆的书,深感他此言不虚。他在古城几乎经历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这里的风光、城墙、市井、古寺、民俗等,都深深地刻入他的记忆里;尤其是打动过他的那些人和事,更是融入在他的血骨中,这如何不叫他从心底发出深情的呼唤与赞美,又如何不叫他在追忆往事时不思之心潮起伏,下笔犹如江河奔涌?
在刘帆的笔下,荆州古城是那么的壮美,古城的人是那么的可亲可爱,他所经历的人与事又是那么的生动有趣。读着他的文字,仿佛就像是跟着他重返遥远的50年代,看到的是一幅幅奇异的古城风情画。

1936年时的荆州古城,解放初期风貌尚未大变
刘帆在江陵师范学校附小读过小学,那所小学的校址就在清代遗留的江陵县文庙内。在他的笔下,那时的文庙是这个样子:“县文庙大门前二、三十米处有石栏杆围筑的外泮池,当地人称学官塘,已经多处頺圯。东西两面与农田、藕塘相连,景色宜人,尤其是莲花盛开,柳枝摇曳时,最令人心醉。学校大门口东西排列的两座石砌大牌坊下有八只巨大的石狮,同学们常常攀援登临,站在石狮子头顶,扯着嗓子吼一声,顿时有了威风凛凛的感觉。迈进大门,又有一高大石牌坊,与校门平行矗立,名曰‘棂星门’,上面浮雕着丹凤朝阳、青龙穿云、鲤鱼跃龙门、瑞草花鸟等图案”“整个校园由东、西两座封闭的庙堂组成。东面的院子很小,仅有一戏台,戏台坐南朝北,台下是石砌放生池……”如今,县文庙那里还是一所小学,当年的大成殿和棂星门也都还在。据说荆州市政府已有意恢复县文庙,如果是这样,那么刘帆在书中的描述,是完全可以拿来作规划时参考的。
在刘帆的笔下,荆州古城内的池塘特别多,也特别的美:“记忆中,总面积四点五平方公里的城区,池塘总数计有数十个之多。”“大片的水域集中在北门至西门,西门至南门沿城墙一带,多因地势积水而成,天成自然,具有浓郁的田园色彩。池连着塘,塘连成湖,岸边绿柳成荫,湖中广植莲藕。春天,听取蛙声一片,观看绿茵铺地;夏日柳丝依依,荷盖亭亭,参差红白两色的莲花,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出淡雅庄重的神韵;秋季,雨打残荷,透着凉意,点点滴滴叩击着心灵,幽远慷慨之情,油然而生”。那一晚,书看到这里就不觉一拍腿,脱口一声:“我的天!这古城美景不就是钱学森倡导的‘山水城市’写照吗?咱荆州早八百年就是这样的!
刘帆的书中还写了一件奇闻异事。1952年,全国掀起镇压反革命运动,荆州为配合运动也要惩处一批反革命份子。这年夏天一日,江陵县政府在城东门内人民体育场召开隆重的公判大会,宣判一名罪大恶极分子的死刑,会后将他用刀砍了脑壳。那人在战争时期,曾亲手杀害过三名赤卫队员。刘帆在书中讲述了他看到的情景:“我呆在场外惊愕地望着涌动的人群,不知所措。突然,‘轰’的一声,如同惊雷炸裂,人群四处逃散,有人在怪声尖叫:‘砍脑壳了!砍脑壳了!’”刘帆挤上前一看:“行刑场是一个荒草丛生的野地,被行刑人躺在草丛中,全身已经用旧布单遮盖,只露出两只瘦黑赤裸的脚杆。旁边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粗大汉子,左手叉腰,右手下垂,提着一把大砍刀,刀上涂满了鲜血,一滴一滴的血珠从刀尖滴向地面。”刘帆还说,行刑人叫韩昌顺,祖孙三代以行刑为职业。他祖父是清代的行刑人,其父继任,身跨晚清、民国两个时代。韩父原本是将这一职业传给韩昌顺哥哥的,可哥哥初次动刀就出师不利,“被行刑者之头尚未砍下,垂下的头复又挺起,双眼直直地瞪着韩兄,韩兄见状,大叫一声扔下刀,撒腿就跑,从此疯了。”韩父无奈地只得将杀人的绝技再传给韩昌顺,他倒是干得不错,可此后心中的沉重与痛苦却无法对人言说。韩昌顺有个独子,到了婚龄还娶不上媳妇,因为没人愿意嫁到刽子手家中,韩家也就此断了香火。

江陵县文庙的棂星门
刘帆在书中写了两个忍辱负重的女人,看过她们的故事,我心中久久难以平静。第一个说的是马寡妇。荆州城内最繁华的街是民主街,街中间有座便河桥,马寡妇就住在桥东北侧的一间破屋里,靠在桥头摆个烟摊过日子。马寡妇人很漂亮,“瘦削的背,瓜子般的脸,柳眉、杏眼、风摆腰”。不少男人常来找马寡妇买烟搭讪,想沾她的便宜,可无不杀栩而归,因为马寡妇人很泼辣:“若是招惹了她,她立刻会双手叉腰,柳眉倒竖,杏眼怒瞪,香沫飞溅,将你骂得五佛升天,六鬼入地,天昏地暗,落荒逃窜。”嫉妒马寡妇的女人们也不少,她们常编造一些马寡妇风流淫荡的故事,将脏水毫不吝啬地泼向她,居然将她变成了荆州城的一个知名人物。马寡妇对这些伤害都尽力地顶着或忍着,不为别的,只为要将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儿子抚育成人。不料有一年夏天里,儿子放学后到校旁的老鸦塘游泳,因双腿被荷梗缠住溺了水,虽然人被救活,却从此一病不起,后来竟一命呜呼了。给儿子送葬那天,马寡妇没掉一滴眼泪。回来后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大喊对不起死去的男人。马寡妇将房门关了三天,大门再被人打开时,屋内空空荡荡,她早已不知去向了。
第二个说的是一个没有亲缘关系,被刘帆称作舅妈的人。舅妈那时很年轻,只有二十八九岁。“人长得好看,鹅蛋形的脸,颧骨略高,扎着两只大辫子,爱笑,待人亲切;勤快,热情,常常帮帮邻居做事。”舅妈的丈夫姓王,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县长,解放后在江陵师范学校当老师,他俩育有两个孩子。1957年,舅妈丈夫当县长的历史被查出来,被关进监狱后的第二年就病死了。“从此,舅妈与先前判若两人,形貌消瘦,衣着散乱,笑容消失。”有一天,舅妈突然对刘帆哭述着说:“王先生是个好人……那年发大水,他驾着船救了不少灾民,我全家都冲走了,是他救了我这个孤苦的女子。”舅妈似乎没有单位,过了不久,沉寂的舅妈突然活跃起来了,盘上头的大辫子又放下来,脸上也有了红晕,但是一些闲言碎语也如影随风地跟着她了。1959夏天,刘帆考上大学来向舅妈告别,舅妈拉着他的手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你会看不起舅妈……我知道自己已经变得不好,但是,我的心是干净的……这两个孩子是他的骨肉,我宁可屈了自己,也不能断了他的根!”在刘帆的笔下,这两个苦命的女人,虽然无依无靠,但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为了将孩子抚养成人,始终坚强地与命运抗争。在一次次倒下又爬起来中,张扬着荆州女人坚忍不拔的性情。
《荆州纪事》里共收录有二十三篇回忆长文,都是通过一人一事来写昔日荆州古城的风情风貌,以及那些早已随风逝去的人和事。在刘帆的笔下,荆州人是美好的,因为脚下有一块养育了他们的美丽土地。
我期待着有一天,刘帆先生能重返荆州,陪他在荆州古城走走看看,听他在回忆往事的同时,又是如何去点评今日的荆州古城。
2024年3月20日写于荆州
打赏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