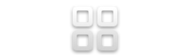沉寂的殿宇
张 俊
1980年仲夏,一个日本旅行团乘一艘长江游轮由重庆去武汉的途中,一个叫中村友胜的团员向中方陪同人员提出想在沙市码头登岸的请求。中方陪同负责人问他去沙市干什么,他说在二战期间,他作为一名士兵曾随部在沙市驻防,在那里也干过一些罪恶的事,为此,他想到沙市的一座大寺庙上香,以表达他的忏悔之意。中村友胜是日本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他去沙市的要求又很迫切,于是中方陪同负责人便安排一名年轻翻译陪同他在沙市码头上岸。
1980年仲夏,一个日本旅行团乘一艘长江游轮由重庆去武汉的途中,一个叫中村友胜的团员向中方陪同人员提出想在沙市码头登岸的请求。中方陪同负责人问他去沙市干什么,他说在二战期间,他作为一名士兵曾随部在沙市驻防,在那里也干过一些罪恶的事,为此,他想到沙市的一座大寺庙上香,以表达他的忏悔之意。中村友胜是日本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他去沙市的要求又很迫切,于是中方陪同负责人便安排一名年轻翻译陪同他在沙市码头上岸。

恢复前的大雄宝殿
到达沙市的第二天,那个翻译陪中村友胜游览了中山路、孙叔敖墓、万寿宝塔等处,而后便让司机开车去松滋的玉佛寺。进寺后,中村友胜说他记忆中的寺庙不是这座,那座古寺很大,特别是大雄宝殿前有一棵古梅树。那个翻译说沙市早就没有寺庙了,目前荆沙最大的寺庙只有这座玉佛寺。听他俩这么说,在一旁接待他们的玉佛寺住持说,这个日本人说的大寺庙应该是沙市章华寺,寺里就有一棵古梅树。中村友胜听了连连点头,说就是章华寺,他要去那里上香。当他俩找到章华寺时,看到的却是一座挤在低矮民居中的工厂。当地居民说,“文革”中寺里的和尚被扫地出门,之后寺庙就改成了沙市无线电一厂的厂房。中村友胜进去看了看,好在那棵古梅树还在,他绕树转了几圈,只能抱憾离开了沙市。
《沙市市志》第四卷这样记载古寺变成工厂的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华寺佛像毁于红卫兵乱锤之下,《藏经》被市六中红卫兵拖走,后存博物馆,造成散失。随即章华寺被无线电一厂占用,无佛教可言。”

无线电厂的厂房(赵楚辉摄)
1966年初,沙市财政部门拨款2万元,指定由市科委牵头,以街道和二轻系统的手工业力量为基础,发展电子工业。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市东方红公社、红卫公社、解放公社(公社相当于今街道办事处)等联合办起沙市无线电厂(后称沙市无线电一厂)。公社办厂没钱建厂房,于是就想到了章华寺,那时寺僧们早已被赶走。1968年,沙市无线电一厂的牌子挂上了山门。
在办厂期间,寺中的韦驮殿成了厂政工组办公室,天王殿改成了生产车间,方丈室设为厂革委会办公室,藏经楼变成职工宿舍与托儿所,大雄宝殿则成了材料仓库。市无线电一厂生产晶体管收音机,虽说是一座街办工厂,但初期产品做得还不错,所产的荆江牌收音机曾在全国同类产品质量评比中获得过第一名,厂子还被评为“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先进企业”。但这座工厂毕竟是土法上马的企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市场对收、扩音机需求量减少,加上该厂的产品元器件质量达不到要求而不得不停产。总之是经过这么一折腾,章华古寺变沉寂了,市无线电一厂也垮了,两败俱伤的结果,至今提起来都令人唏嘘。
明正德年间,有个叫崔桐的人来到沙市,崔是进士出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是个饱读史书的人,公干之余想去看古豫章台遗址,可找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有看到,一切都湮没在历史尘埃里了。后来,他颇为遗憾地写了首《豫章台·七绝》:“沙市黄鹂啼暮春,落花残雨净轻尘。旁人指点章台路,烟草微茫认不真。”其实,人对久远的往事“认不真”是件平常事,崔桐如此,中村友胜也是如此,今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万事万物逝若流星,在模糊不清中去品味一些事,或许更能体察出一番新意来。

大殿前堆满建材(赵楚辉摄)
佛陀认为“诸行无常”,兴建于辽代的北京西山佛牙舍利塔砖上刻有《法身舍利偈》:“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三千大世界,一切因果促成的变化都是此有彼有,此无彼无,流迁变动,永无穷尽。宇宙中一切物质的生成消灭,都逃不躲“成、住、坏、空”四个字。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章华寺变工厂的事,那些在非常时期被赶出寺门的章华弟子,其心应是宁静淡泊的,只要佛祖在心中,其他都在其次。
(选自《章华寺的钟声》 摄影 江永武)
打赏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