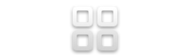身体:权力全新的竞技场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书评
(选自《中华建设》2018年12月刊 作者:安提戈涅)
在齐美尔眼中,建筑物被赋予了高度抽象的哲思性。以桥与门为例,它们意味着两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客观事物对我们具有两重性,自然界中所有事物既可视作相互联系,又可视作相互分离,物质的不断转化——譬如能量——将一个物质与另一个物质联系起来。万物转化无穷才创造出宇宙。”因而,桥梁的美学价值在于,它使分者相连,它将意图付诸实施,而且它已直观可见——从桥上看,两岸风景都可收入眼中。在统一与分离的关系中,门则偏向后者,它以几何形式隔离了内外空间,闭合出某种“离奇的、自我局限”的生活。齐美尔所要强调的,是由建筑物所体现出的界限的意义和价值:出,可仰观天地,退,可俯察内心。出于人的“心灵、精神上的性格”偏好,人与城、人与建筑达成一种和谐自足状态。
但是,在当代理论界对身体的的兴趣呈井喷式爆炸后,对城市建筑的考察也打破了抽象哲思的“界限”、更使得肉体与建筑的和谐自足关系一变而为被操纵、被设计与被筹划。一如《肉身与石头》一书以眼花缭乱的方式所呈现出的——身体与城市(所谓石头)形成互相镜像的模式,无论是从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空间跨越到罗马基于视觉时序的国家想象、抑或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城进入近代多元文化的中心纽约,城市与肉体的关系变为互相影响,互为烙印,手持通红烙铁的,却是远不可以却无处不在的权力。必须首先厘清权力的概念,它是贯穿全书的核心线索——毕竟这本书,是福柯的、太福柯的。
权力观念及其分析方法,是福柯思想影响最大的遗产。在《性经验史》中,福柯完整的定义了“权力”的概念:“我不想把权力说成是特定的权力,即确保公民们被束缚在现有国家的一整套制度和机构中,”他也不建议把权力理解成一套普遍的控制系统,而是应该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他们内在于他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他们的组织……理解社会领域的格式,千万不要在某一中心点的原初存在中,在唯一的最高权力中心寻找它,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这种权力经验如空气般渗透入一切日常生活的缝隙。在其他作品中,他也自觉地以同一主旨的诉求构筑出统一的基调——无论是大至监狱成系统的规训体制或是小至厕所的门板安排、写字时握笔的规则;无论是借理性之名对疯癫者进行的肉体规划艺术或是在技术与疾病白刃相交时理性语言所照亮的医学密塔——它们都渗透着权力的秘密。这意味着,社会所内嵌的各种各样的实践与组织形式、权力艺术的历史悲喜剧都把目光投向了身体。身体不再是主体性的(如笛卡尔所坚信的),也不再有生产性(如德勒兹所认定的),它是终极权力水域所抵达的岸头,被夹杂着编码之沙的浪潮频频冲击,它等待着权力的篡改、铭写、矫正、宰治。一种新的历史传统就此生成:身体一脸仓皇,权力高歌凯进。
理查德.桑内特笔下的城市建筑,作为权力的世俗实在代码,却颇为诡异地稍微放松了对肉体围剿。他承认,“都市发展的过程中,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象常常以“变形”的方式来界定建筑物或整座城市应该是怎么样。”但是同时,肉体的特质因素也多少反射到了城市的规划变形上,也就是说,理查德.桑内特从福柯的理论出发,灵机一动地又暗中将德勒兹招至麾下。德勒兹抽去了身体的具体内容,将其抽象为一种生产性力量、生产性欲望。因而,我们看到桑内特的身体,不仅是被生产的,也是生产的——当然,这生产的结果往往是消极的,它极为悖谬地助益了石头对肉身进一步的规约。
理查德.桑内特对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犹太区的考察最具有说服力。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对犹太人态度真实地反映了其时居住于威尼斯的犹太人处境,中古名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在犹太人读来却颇显苦涩,他们“可以在城市里做生意却并不代表更多的自由。犹太人在交易时也许与别人是平等的,但在居住上却被完全地隔离了。”德勒兹身体的生产性开始发挥效用,桑内特描绘到:“当威尼斯人把犹太人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内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隔离一种会传染到基督教社团的疾病,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特别会有一种令人腐化堕落的身体邪恶。”犹太人被文化力量塑造出的身体不洁性引发了种族间的焦虑,商业上的一个小规矩可见一斑,基督徒完成交易是以握手或吻表示结束,犹太人却只是隔着空气鞠躬。这种身体引发的焦虑大肆蔓延,渐渐的,麻风病、梅毒、性病都被视作犹太人的种族病,身体固然产生了一种力量与欲望,却是反方向地推动着基督徒进一步将犹太人圈在某个空间中。起源于铸造厂(gettare)的犹太人聚居点演化成如今在犹太裔作家笔下频频出现的“阁都”(Ghetto),正是威尼斯城中这一由石头力量堆叠出的新空间开启了犹太人被绝对隔离并自生自灭的都市身体体验。桑内特使我们颇为哀痛地感受到对德勒兹的反讽。
此外,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中街道与人体交织关系的梳理,理查德?桑内特再度阐释了福柯+德勒兹的双重命题。医学家哈维改变了人们对都市环境方面的期望与计划,因为正是他于1628年发表的《心血运动论》引动了对身体理解的革命,他发现的血液循环、健康状况引导出公共卫生上的新观念。18世纪的启蒙者便运用了这些观念来设计城市。“设计者想让城市变成一个人们可以在当中自由移动与呼吸的地方,在一个由流动的动脉与静脉的城市里,人们可以像健康的血球一样川流不息。”城市规划面貌一新,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欧洲城市开始从街道上清除尘土……街道下面,城市的‘静脉’取代了浅陋的污水池,巴黎的下水道可以将脏水与排泄物运到新的下水道河。”如同启蒙走向其背面一般,取自身体寓意的城市筹划在接受了身体赋予的“生产性”的灵感后,却倒打一耙,对身体产生了新的伤害。新的城市规划与资本主义发展、个人主义滋生相伴相随,静脉与动脉的交错继承了威尼斯城市中“阁都”的歧视意味,只不过是将种族换成了阶级,这一次,被划分到规划优良的城市空间之外的,是大批城市群众——“在都市改革者关于公共卫生的论述中,城市群众则是病菌的滋生原。”各种朝向文明优美的城市改革浪潮都设法将群众“堵”在外面,宏伟是它的宏伟。它下面却是挨饿、巴望着高价的粮食与受苦的肉身状态。
城市与人的主题是传唱不休的,但它的主题未必总令人感到宽慰。马歇尔.伯曼早已有言在先,“虚构和现实的人的生活——一切都体现了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他对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林荫大道的考察、对欠发达的城市彼得堡中涅夫斯基大街的细描,把肉体与石头的关系引向令人爱恨交织的现代性体验上;而理查德.利罕对城市的观测则指向了城市与文本的交界地带,那里歧义丛生,启蒙的遗产与诗人的诗行双双构筑着对“知识与文化的历史”的考量——至于理查德?桑内特,他在福柯开创的谱系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却并未使权力与身体的等级状况有所转机,德勒兹有关欲望政治学解放身体的策略如气球般被一放而空,权力镰刀过处,兵不血刃。
(选自《中华建设》2018年12月刊 作者:安提戈涅)
打赏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