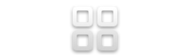故乡的枣树林
中华建设网讯(鲁连静) 五月,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阳光明丽,田野碧绿,连空气也是新鲜的,耐人寻味。不知为什么,每年的这个时候,无论是多么紧张的课程,或是多么繁忙累人的考试,我总是身不由己地踏上通往故乡的归途,带着一个异地游子满身的尘土,带着一个远方儿子眷恋母亲的拳拳之心,以及对一个已故老人的思念之情和满眼负疚的泪水。

我回来了,妈妈;故乡,我回来了。你会欢迎这个不孝的儿子吗?
徘徊于家乡的枣树林,我轻轻地呼唤着那位长眠于地下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他坟头上一簇簇在春风中颤动的小花。十年了,在众多村民的心目中,老人的名字早已暗淡、消失了,就连和他很要好的我的父母也不常常提及他了,也许,他们都忙于活计了吧!可我,一个昔日的“光腚猴子”,却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老人,不会忘记他身边这片密密匝匝的,充满着神秘色彩的枣树林。祭奠老人,本应在清明,而我却把它推迟了,选择了五月,------枣树发芽的季节,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只知道嫩芽象征着浓绿,浓绿象征着硕果,而累累硕果,就是我的希望和追求。这里有成片的枣树,也有我的亲人,有令我梦魂牵绕的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它们滋养了我,我知道我的故乡从来就不缺少浪漫。

我用家乡肥腴的黄土,给熟睡的老人穿上“新衣”,我觉得心情舒畅极了,望着满坡枣树粗壮的躯干、高大的树冠,望着枝桠间刚刚萌动的星星般的绿芽,我的心情,又怎能平静下来呢?
家乡傍依在徒骇河畔,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枣园”,难怪同事们听后还说真能嗅到一股清香的枣花味道,我真为此感到自豪!是的,我的家乡有太多枣树,村前村后,村内村外,一棵棵,一片片,五月的家乡,好像淹没在枣花香郁的浓汁里,假若你能在夏末初秋来到这儿,你肯定会饱尝枣子的口福的。“枣园”名之谓“园”,其实比“园”大得多,可以说是枣林,整个是一个枣树的绿色海洋。

村后的这片枣林,可算是家乡枣林的首席代表了,或许是徒骇河的滋润,枣树长得特别高大、茂密。不但树大树多,枣树的品种也很多,有核桃般大的“婆婆枣”、“面仁枣”,有小如珠丹的“酸枣”、“脆枣”、“沙枣”,也有长得奇形怪状的“奶头枣”,其中要数“奶头枣”最为可口了,鲜红铮亮,形似奶头,尝一颗清脆甘甜,能把你甜一溜跟头。但是,唯一有这种枣树的那片枣林是集体的,平时大人们干活了才可以进去,而我们这帮“小把戏”是不允许进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时常与看林的“尕胡”老头儿发生冲突。

“尕胡”老汉,个子不高,约莫七十多岁年纪,面目清瘦,从他那刀削般的深深地皱纹和棱角分明的黝黑面颊上,可以看出他一生饱经了许多的沧桑,但是,他很爱说话,由于嘴巴下蓄了一撮“山羊胡”,因此而得名“尕胡”。这是我们小孩对他的戏称,大人是从不这样叫的。他的大号叫张炳栓,大人们都叫他“柄栓叔”或“柄栓爷爷”,老人并不是本地人,有人说他是北乡人,也听有人说他是南方人,至今我们都不知他老家在何方,老人自己从不提起这桩,人们只知道当年他跟着部队打过几次仗,负了伤,后来就一直住在我们村,已有三十多年了。他没有妻室儿女,生活简朴,待村里人极好,特别是对孩子们,每到夏秋之夜,我们都喜欢到他院子里的大枣树下听老人讲三国、啦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们也给他唱奶奶教的歌谣,可热闹了!老人不知何时学的治病的本领,村里人有个小病小灾,从不去镇上看医生。因此,村里人都很尊重他,不管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都要请老人坐阵,有时这家包了饺子,那家扎了米粽,也总是忘不了他老人家,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不知何时起,由于大队的枣林无人看管,老人就搬到林子里去了。大片枣林中间,坐落着一间孤独的小土屋,一张简陋的铺板,一口用三块砖头支起的生铁锅,便撑起了老人寂寞而清静的悠悠岁月。

每天清晨,老人起得都很早,伴着林中早醒的鸟雀的欢噪,升起了那缭绕在枣林上空的第一缕炊烟,就像绿色海洋中的一片白色孤帆,然后,便随着富有节奏的拐杖的击地声,绕着林子一圈圈地转,好像在寻找着什么,直到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每天黄昏,他站在林边的徒骇河边,眼望西方,默默地注视着渐沉的夕阳和那漫天血红的落日余晖,又像在思索着什么------。
夏日里,是老人最繁忙的季节,他把由于暴风雨吹落在地上的枣子,一颗颗捡起、洗净,在那并不能容纳更多的小生铁锅内一锅锅煮熟,然后,把枣子挨家挨户地送给村里的人家,也就在这时,老人的脸上才能泛起可爱的神奇的红光,此时,他会笑眯眯地向人们喊:想再吃,自个儿携去好了!随着他由于缺少牙齿而发音不准的话语,铜锅烟袋在唇上一翘一翘的,煞是可爱。
也就是那年的秋天,枣子结的特别多、也特别大,我们吃腻了自家树上又大又涩的“婆婆枣”,眼瞅着“尕胡”老人林子里的“酸枣”、“奶头枣”流口水,又不情愿和他要,于是,我便叫了胖墩、三坏几个小伙伴,准备来个“泥猴偷枣”。
那天,我们偷偷地发现老人进了屋,便一个个跑进林子,迅速地爬上了枣树,啊!多馋人的小枣啊,我们尽量往胸前早已被扎起的背心里塞,忽然,一个声音在树下大喊,我低头一看,完了!“尕胡”老汉正怒视着我们,大声地吼叫,手中的拐杖在空中挥舞着,像要抛来,三坏见此情景吓得尿湿了裤子,我也因慌张被树枝擦破了双腿,哪里还顾得上疼,老汉早已拿走了我们脱在树下的鞋子,我们只好赤脚下来,一路狂奔------。我还从未见过老人这样愤怒过,预感到事情不妙。
晚饭时,我们才敢回家,显然,“尕胡”老汉已经来过,鞋子在窗台上搁着。爸爸看着我血淋淋的双腿,二话没说,狠狠地给了我两个鞋底,我不敢哭,心里只是骂“尕胡”老汉。从此,我便和“尕胡”老汉记下了“仇”,总想报复他一回下。
几天以后,听妈妈说柄栓爷爷的榆木拐杖不见了,而且屋门上的锁不知谁塞进了东西,插不进钥匙了------。我心里明白,我还觉得不解气,就和三坏一起,在老汉常走过的林间小道上,偷偷放了一截从附近搬来的大树墩------。
第二天一大早,就听爸爸说,柄栓爷爷不小心摔坏了腿,挺厉害,爸爸要带他到城里看医生。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匆匆吃完早饭上学去了。
从那以后,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到村后那片枣林去,也没有再看到“尕胡”老汉。一年以后,我升了初中,便到更远的镇上念书了。时光如梭,随着年龄的增长,家乡的枣林和那惊险离奇的童年生活在记忆里渐渐淡忘了,偶然想起,也只是作为一则笑料,引不起更多的联想。
一个细雨朦胧的下午,我从学校回到家中,就听有人说柄栓爷爷死了。爸爸妈妈先奔了出去,我也跟了出去------。小屋前挤满了人,没有人说话,在几个村干部的招呼下,人们把老人安葬在林子的东部,靠近河畔的地方,除去几个和他生前常在一起的老人为之唉声叹息之外,没有更多的人为其永别而过分悲伤。我含着眼泪跟着送葬的的人们,看着“胡子”爷爷默默地消失于这个世界,想起他凄凉孤独、清贫残缺的一生,想起他为孩子们送熟枣子的喜悦和夕阳西下时他那暗淡的寂寞,以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对他不堪一击的生活施下的罪孽和淫威。我震惊了,霎时,好像有无穷的累债压迫着我的胸膛、我的心灵,使我难以呼吸,我感到我的心在滴血,我满眼泪水,不敢再想下去:“张爷爷,张爷爷,爷爷!”我哭着、喊着扑向老人的坟头,我想把满肚子的悔恨哭出来,要让老人都听到,可是最终还是被大人们拉走了。我清楚记得,那个阴雨霏霏的季节,正是枣花盛开的五月!
从此,在这个美丽的、童话仙境般的枣园小镇上,在这片弥漫着家乡特有气息的枣林里,我埋下了自己不能抑制的忏悔的种子,用来弥补我的过失、我的阵阵悲哀、和那片深深地怀念------。
啊!面对可爱的、久违的、遥远的故乡,面对眼前这大片的经历了风霜岁月渐渐老去还在奉献累累硕果的我故乡的枣林,面对久已长眠在家乡肥沃土地的令我不能平静下来的孤苦老人,我百次千次的忏悔:能原谅我这个十恶不赦的逆子吗?
五月的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枣花落了一地。

作者:鲁连静,66.8生,笔名陆宁,喜欢写作,现居德州,与君共赏。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