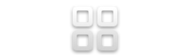从《城市发展史》到《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
—《城市发展史》书评
在下意识的理解中,城市的繁荣似乎宣告着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也预示着同田园牧歌般昔日往昔的挥手作别。城市生活,以其特有的开放、自由、新颖、丰富以及伴生的冲突、混乱、紧张、不安,居于现代性的核心部分。由古至今,无数的思想家从各不相同的侧面,对不同历史切面上的城市进行了思索,其中称颂有之,贬斥也有之。而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则以整个人类历史为尺度,试图以城市这一线索,打通文明曙光初现的两河流域到冷战阴云笼罩的全球化世界。这当然是极具野心的尝试,而这种宏观的视野不仅揭示了时间长流中不断发生在城市中的嬗变,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刺穿这种不断嬗变的迷雾,以揭示其下某些稳定存在的方面。
(全文见载于《中华建设》杂志2019年4月刊,作者:余沐洋)
在下意识的理解中,城市的繁荣似乎宣告着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也预示着同田园牧歌般昔日往昔的挥手作别。城市生活,以其特有的开放、自由、新颖、丰富以及伴生的冲突、混乱、紧张、不安,居于现代性的核心部分。由古至今,无数的思想家从各不相同的侧面,对不同历史切面上的城市进行了思索,其中称颂有之,贬斥也有之。而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则以整个人类历史为尺度,试图以城市这一线索,打通文明曙光初现的两河流域到冷战阴云笼罩的全球化世界。这当然是极具野心的尝试,而这种宏观的视野不仅揭示了时间长流中不断发生在城市中的嬗变,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刺穿这种不断嬗变的迷雾,以揭示其下某些稳定存在的方面。
芒福德在起笔之处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人类历史刚刚破晓时,城市便已经发展到了成熟形式。”
这种判断已经不满足于将城市的形象从工业时代的创作拨回为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破晓前”,为城市罩上了一层“文明开端”的神圣光晕。这种神学色彩的处理在全书的末尾得到了呼应,芒福德目睹现代城市文明的重重危机--城市的拥挤与盲目扩张、都市组织机构对人自我的抹杀、城市居民间的猜忌和误解,这种紧张状况无疑与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性相扣合,并最终孕育着在地平线浮现的核战争末日。而面对这种敌意与危机,芒福德的目光恰恰落在了“历史之前”的古代城市。其反应或许点染着基督教启示录的意味,在这种呼应之间,古代城市成为芒福德眼中“失落的天堂”,是人类出走的伊甸园,也是人类文明走过5000年的历史之后应当回归的起点。他认为:“因此,在我们时代,城市如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恢复古代城市(特别是希腊城市)所具有的那些必不可少的活动和价值观念。我们的精巧机器所播映的那些仪式场面,不能代替人类的对话、戏剧,不能代替活的伙伴和同事,不能代替友谊社团。”
很难不注意到这种论述同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论及的“灵韵消散”之间的惊人对立,本雅明在书中写到:“如果在所有艺术中,是戏剧最明显地陷入了危机,那么,这便是由其本性使然。因为彻底地由机械复制去控制的艺术作品--例如电影--与舞台的对立就再明显不过了。在舞台上,演员的演出每次都是新鲜的……而电影演员则往往做不到。他的成就并不是一个统一于一体的成就,而是由众多的单个成就组成的。”
有着同样观察的芒福德和本雅明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芒福德固守着本真的仪式场面,话剧、活的(毋宁说“在场的”)伙伴和同事,而本雅明则对这种态度多少流露出奚落,在评价里格耳和威克霍弗时,他说:“尽管他们的认识是深刻的,但他们仅满足于去揭示晚期罗马时期固有的感知方式的形式特点。这是他们的一个局限。他们没有努力--也无法指望--去揭示由这些感知方式的变化所体现的社会变迁。”
在某种程度上,芒福德对城市的理解是一种文化本位的。他在开头提出了一种城市起源的宗教解释,文化对于城市的统治地位在其看来贯穿城市史的始终,却在现代被经济开发的要求所篡夺。这无疑于本雅明的唯物主义立场背道而驰,因而芒福德“复兴古代城市”当然也遭到本雅明的奚落。
但现代性危机的问题终究需要得到回应,而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全景缩影,对于现代城市的批判构成了答案中的关键步骤。本雅明的“城市观相学”,正是在这一相同问题意识中开出的另一条路径。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本雅明通过重新打开波德莱尔的诗作,将巴黎视作一个辨证意象,试图从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的面孔中“相”出巴黎的性格和命运。在这项未完成的工作中,巴黎显现出童话与梦幻的面具装点之下的另一幅面孔,眉目间写满了后革命时代的犹豫和彷徨。大革命、拿破仑、王政复辟、僭主和共产主义接踵而至,终于在流干了一个世纪的鲜血之后,巴黎不仅变卖了血统和封建制度,也变卖了启蒙、理性和美德。金钱化约了一切标准,它以其绝无仅有的公正性和精确性带领巴黎走向了时代的最前列,也使这座城市加冕为本雅明笔下的“十九世纪的首都”。
而巴黎绝非独享着自己的命运,这杯散发着铜臭的毒酒会依次传到纽约、上海、东京、马尼拉和西雅图的面前,而他们自己,也甘之如饴。
这种传统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继承,大卫哈维在《巴黎,现代性的首都》(或译《巴黎城记》)中试图补全本雅明的拼图,引入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和杜米埃的漫画等材料,却只是展现出一幅更加鲜血淋漓的画面--在银行家投机下无力支付地价而破产的小业主;旧城改造中不能负担房租而流离失所的工人;道路拓宽的目的是让拿破仑三世的大炮更容易瞄准起义的战士;而木板路被替换为石子路更是为了防止公社战士就地获得建筑街垒的材料,最后,在五月流血周的屠杀中,圣心堂高高伫立。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解剖“超级市场”这种空间结构是如何塑造着我们的城市整体和居民的日常生活;列菲弗尔则直接指出“20世纪,现代性扩展到整个世界的动力……是国家地理性规划下以空间生产为基础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徳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管理和生产空间建立一个总体性的、无所不能的控制体系。”到最后,阿甘本把都市(Metropolis)和城市(City)相区分,认为后者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概念装置,统治者的规训与空间治理消解了城市居民的主体性,城市生活成为另一种流水线上的机械重复,快感的满足和惊颤体验成为了当代的祭祀盛典和公民大会。
回到《城市发展史》,毫无疑问,芒福德和本雅明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共享了相同的问题意识,即浮现的现代性危机。尽管有堪称惊人的资料作为支撑,但在向结论迈进的道路上却流露出某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疲乏。一方面,文化与资本的战斗中,我们已经见证了前者无数次失败,另一方面,盛大的公共集会--在当代无非是艺术展,演唱会,体育比赛--坚定的扮演着资本共谋者的角色。芒福德小心翼翼地试图从城市入手,拯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但给出的答案似乎总无法令人信服。或许正确的道路只能是反过来,从对资本逻辑的爆破入手,城市才可能得救。
(全文见载于《中华建设》杂志2019年4月刊,作者:余沐洋)
打赏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